摘要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争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关于战争的各种观念、各派势力的宣传竞相登场、展开角逐,现代杜诗学就参与这场舆论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衰败景象,促使梁启超重新思考中西文化问题,发表《情圣杜甫》的讲演;20年代国内军阀混战,激起“非战运动”,“非战”思想也贯彻在当时的杜诗研究中。“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争性质发生变化,不同的政治势力持有不同的战争观,并影响到各派学者的杜诗学研究。重庆国民政府、汪伪政权、延安文艺界和各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并受其影响的学者,从各自的政治立场、战争观念出发,对杜甫战争诗作出不同的评释。回顾这段学术史时,不能笼统地看待杜甫“非战”说,须要进一步探究言说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动机和社会效果,作出具体的剖析。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文学不可回避的素材,同样,文学研究也关注着这一主题,并受之制约和影响。中国古代杜诗学的盛衰,就与社会治乱、朝代兴废有着紧密的联系。 过去百余年,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中走向胜利、走向独立。战争是近现代中国的严重问题,也是各种文化思潮的基本背景。研究现代中国文化,难以回避战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衰败悲惨景象,令国人震惊。随后国内的军阀混战,激起了人们的非战、厌战情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掀起国内抗战热潮,而不同的政治势力,对抗战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种种关于战争的观念,都曾直接地影响到现代杜诗学。战争本来就是杜甫诗歌的基本主题,现代学人在阐释杜诗时表达了各自的战争观,甚至借杜诗宣扬自己的战争理念。 杜甫素描像 一、“欧游心影”与《情圣杜甫》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社会的严重破坏、经济急剧衰退,这促使思想文化界进行反省和转向。这场战争也给予中国思想界以强烈的震动。1920年梁启超游欧归来,发表了著名的《欧游心影录》。欧洲一战后的凋零荒废,令人触目惊心,詹姆斯、柏格森等人的新人文主义又燃起他新的希望,促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他感慨“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否定科学万能,强调人类的互助互爱,重新反思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中“尊德性”的部分表示更多的偏爱和肯定,更重视文学的美、趣味、人性意义和人格价值。如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说:“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认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与维新运动时期鼓吹文学界革命的梁启超几乎判若两人。 梁启超照片 正是在这种思想转向之后,梁启超于1922年5月21日在诗学研究会发表了《情圣杜甫》的演讲,对杜甫其人其诗作出别具一格的解读,是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杜诗学论文,在学术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杜甫被宋人尊为“诗圣”,作为忠君爱国的诗人典范,历代诗人奉为至尊。但是一战后的梁启超,对国家主义观念有所节制,更多地宣扬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观念,梁启超笔下的杜甫,不再是忠君爱国的化身,转而成为“中国文学界的写情圣手”,梁启超称之为“情圣”。梁启超列举诸多诗例,说明杜甫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对兄弟、姊妹处处至性流露,爱情秾挚,对朋友多情,泛爱生物等。此前,袁枚曾说过杜甫“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但是,像梁启超对杜甫诗歌的情感作如此深刻透辟的阐发,在杜诗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梁启超如此讴歌赞美杜甫的至性真情,就是希望“这位情圣的精神,和我们的语言文字同其寿命;尤盼望这种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现代青年文学家的脑里头”,也就是要发扬优秀传统艺术的价值,修养当代人的情感,往高洁纯挚方向上提挈,以矫正科学至上、国家主义等现代观念的偏颇。 文本的意义永远在建构之中。从“诗圣”到“情圣”的转变,是传统政教文学观转向现代抒情文学观之后对杜诗的重新释义。正是通过不断地重新释义,传统才能融入当下变得鲜活起来,现代理论才能获得传统资源的支撑。不过,国内军阀混战和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没有为梁启超的“情圣”论提供适宜的社会基础,现代杜诗学并没有按照“情圣”论的方向发展。 二、“非战运动”与杜甫“非战”诗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饱受战争的苦难。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和平与安宁,随之而起的是十余年的内战。军阀混战搅扰得中国无片时的宁静,满目疮痍的现实迫使有识之士起来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自20世纪20年代,“非战”运动声浪日高,成为时代的主潮。“非战”运动的兴起,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1924年4月,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到中国发表演讲,宣扬大爱和良知,反对暴力。这对于“非战”运动在青年中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1927年6月,法国外长提议法、美永好,得到美国的响应,欧美国家签订了《非战公约》,后扩大范围,共46个国家加入公约。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加入了这个公约。《非战公约》的内容,一是极端排斥以武力为政策之工具;二是以和平代武力,来解决国际的纠纷。《非战公约》促进国内对于“非战”的讨论。其实公约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各国都在扩充军备、增强武力,因此“世界大战仍恐难免”。日本虽然加入了“非战公约”,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引发了“九一八”事变。这次事变在国内思想文化界再一次掀起了“非战运动”的高潮。 文学界积极参与了二三十年代的“非战运动”。1924年8月,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小说月报》推出了“非战文学”专号;当时,外国作家如托尔斯泰、莫泊桑等的非战思想和非战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中国,出现了一批以“非战”为主题的小说。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的非战主题、非战思想也被有意识地挖掘出来,以响应时代的诉求。正如当时政府发布的《我国赞同非战公约照会》所言:“今日之非战公约,在我国视之,直无异发扬先贤之遗训,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者是也。”的确,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抗侵略,传统文化中“非战”资源十分丰富。当时出现了不少阐述中国古代“非战”文化和文学的文章,其中以阐发和演绎杜甫的“非战”诗歌为最多。刘尚达将杜甫的《石壕吏》演绎为短篇小说,最后附言说:“我写完了这篇《石壕吏》的演义,知道兵即是匪;更想那‘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的句子,真是有今昔一致的感慨!”俞宗杰将《石壕吏》编为独幕历史悲剧,发表于《京报副刊》1925年第342、346期。这是当时青年学生以编剧方式宣扬杜甫的“非战”思想。文学研究会的年轻成员顾彭年撰著专书《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于1928年出版,在《序》中他说:“迨江浙战争发生后,作者对于战争的恶魔的面庞益认识清楚,这位大诗人的非战作品,也就愈加涌现在我的脑际了。”正是对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灾难局面的严重关切,促使他撰著此书。作者剖析杜甫诗歌所揭示的长久战争、寇盗充斥、镇将专横与兵制腐败等弊端,这些与其说是唐代社会问题,不如说是现实中的积弊。 但是,是否所有的战争都应一概反对呢?显然不是!“非战运动”只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和平吁求,本身并非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正确方法。一味地渲染战争带来的苦难,只会散布消极、颓废情绪,削弱被压迫者的抗争意志,不但不能阻止军阀放下屠刀,甚至可以说是施暴者的帮凶。当1923年初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工人士气消沉之时,当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之时,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时,如果只是搬演《石壕吏》的惨剧,只是在鼓吹“非战”文学,那就是民族精神的颓丧、沦亡。在这个看似学术的问题上,是有思想交锋和政治斗争的。当时有几位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对于“非战文学”的理论思考显得更为深刻。曾任上海总工会秘书的魏金枝撰文分析说,战争有两种:一种是从那些私人的手里夺其所有到这些私人的手里的战争,一种是从那些私人的手里夺其所有到民众的手里的战争;也就是说,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历史上看,既有非战文学,也有投笔从戎的文人,并非文人都是非战。根据战争的目标,应该有两种文学:一种是非难不义之战的,一种是鼓吹革命战争的。他评论当时国内“非战文学”的功过,说: 魏金枝(1900—1972),原名义荣,黄泽镇白泥坎村人。 间接有指出军阀对于民众的暴行,可以激动民众对于暴行的抵抗;然只给民众以消极的厌乱的观念,与其说能有益于革命事业的进步,不如说是增进民众的厌世色彩的正确。……非战文字本来是种反抗精神的表现,决不是感伤主义的文学可以代替……固然,目今中国是陷在多种战的炮火中,一时不易逃出这炮火的重围,一面应该有非战的文学出来替人民诉苦,但一面也该指示人民以鉴别战争的方向,须以反抗不义战争的力量,培养真正战争的勇气。不然,我恐非战文学将列入颓唐主义文学的旗帜下,失却了反抗精神与革命精神的色彩,而结果更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刀枪之下,造成更多的呜咽的悲声,与被损害的可怜的众生而已!” 非战文学不能只渲染感伤主义,陷入颓唐厌世。它应该是对不义战争的谴责,是对正义战争的支持和鼓舞。在恽代英等人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金元,也撰文分辨战争的性质,说:“为自私、为压迫人家而战的‘战争’,是要不得的;为向着争自由而战的‘战争’是千万要得的。血,是自由底代价呵!”当你在叫喊和平非战,“吴佩孚辈正枕戈而冷笑着呢”!战争本身具有正义与邪恶之分,如果不认清战争性质而一味地反对战争,过分地宣扬战争的惨烈,渲染战争的破坏性,会在民众中产生削斫士气、挫败斗志的消极后果。 特别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的性质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在被侵略被占领的国土上宣传“非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民众涌起抗日怒潮、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之时,南京当局一再退让,奉行不抵抗政策。这种社会意识的分裂就表现在当时对杜诗“非战”的评论上。绍禹还在阐述、张扬杜甫的非战思想,认为这是杜甫的国民意识。当时人们阐论杜甫的非战诗歌,一般重在突出杜诗对战争的破坏性、悲惨性的抒写,把“三吏”“三别”等都解读为反对战争的诗篇。班文茗则指出,杜甫并非一味地非难战争,“杜工部所反抗的,乃是穷兵黩武的外征,和兵祸连年的内战,如果遇着敌人侵略边围,他仍是主张血洒疆场,奋勇杀贼呀!爱国而不流于黩武,这是研究杜甫思想者所宜注意的”。这样的分析更为辩证,既能具体辨别杜甫战争诗的不同性质,契合杜甫诗歌的实际,也寄予了作者对当下政治问题的关注。这样的研究,就是激活了传统,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将现实思考蕴含于历史叙述和评判之中,在历史中映照现实。 三、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杜诗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打响了,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日本军国主义者采取“以华制华”手段,于1939培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投降派,后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汪伪国民政府”,宣扬和平建国。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也是道义、信念、士气、斗志乃至整个民族意志和精神的较量。“批判的武器”在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延安红色政权、重庆政府、汪伪政权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都重视思想文化宣传,重视利用文学研究来表达各自的战争观念,影响民众。 (一)重庆国民政府治下的杜甫论 新的战争形势促使当局对“非战文学”作出批判性反省,在杜诗学上,体现为对杜甫相关诗歌的歧解。1938年初教育部颁布禁令,禁止杜甫《兵车行》《石壕吏》一类文字充为教材。杜甫《兵车行》《石壕吏》等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均被解释为“非战诗歌”,揭示兵役之苦,这对于1937年底的抗战形势是非常不利的。1937年冬,湖南汉寿县党务指导委员会采纳王金才的提案,称杜甫《兵车行》《石壕吏》等诗歌,削弱士气,妨碍征兵制度的实施,应严切禁止发行,以鼓励民气;呈文提出应选择《国殇》《满江红》之类鼓舞斯民同赴国难的作品,加以选择,辑为专书,俾供传习。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接此呈文后,发布《国民政府军委会宣传部致教育部公函(武字第一一九号)》: 查有唐诗人杜甫所作《兵车行》《石壕吏》等一类文字,虽有非战思想,然系描写专制时代君主开疆拓土及官吏扰民之作,与现时对外争民族生存之战争,不能混为一谈。且此项作品,流传已久,未便骤予查禁。唯值兹对外抗战厉行兵役时期,各级学校,如采用此类作品,充为教材,实非所宜。除关于原呈所请选辑鼓励民气文字部分由部另案办理外,……转令各省市教育厅社会局,饬知各学校,不得选录非战文学作品及文字充为教材,并由各该厅局负责监察检查。至已故邵翼如先生所辑《军国民诗选》《民族正气文钞》,在鼓励民气文字未编定以前,可核令各校酌量选用,至纫公谊! 国民政府军委会宣传部认为杜甫《兵车行》《石壕吏》等“流传已久,未便骤予查禁”,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不适宜于充为教材,因此致函教育部,告诫各级学校,不得选录非战文学作品及文字充为教材,并提议暂时选用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编纂的《军国民诗选》《民族正气文钞》作为教材,以鼓励民气。于是1938年2月,教育部颁布训令:“各校不得选录非战文学作品充为教材,以邵元冲先生所编《军国民诗选》《民族正气文钞》等书可令各校选用。”《军国民诗选》选辑自《诗经·秦风·无衣》以来历代忠烈之士慷慨激昂的爱国诗词,希望激励国民同仇敌忾,以挽回民族的危运。《民族正气文钞》选辑自宋以后历代忠烈的63篇文章,表现中华民族激昂伟大的正气和果毅刚劲的美德。从20年代的“非战”文学热到1938年政府以行政手段禁止杜甫《兵车行》《石壕吏》而提倡这两部诗文选,正显示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当局重视用文学来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而使之服务于抗战动员。 杜甫是不是一个“非战主义者”?《兵车行》《石壕吏》之类诗篇在抗战建国中是不是只会发生消极影响而应该禁止呢?在凝聚民族精神、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时,杜诗是否毫无意义呢?当时的一些学者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给予杜甫诗歌新的阐释。 在重庆国民政府里任过多种文化宣传职务的“三湘才子”易君左在1939年发表了《杜甫今论》,主旨在消极地纠正“杜甫是非战主义者”的论调,积极地提出“杜甫是抗战神圣论者”的命题。他提出,杜甫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一切人事上的批评也都是为国家的,“国家至上主义”是杜甫“革命主义的人生观”的生命基石。1942年,易君左又发表《杜甫的时代精神》,对于一度被解释为“非战文学”甚至禁止选入教材的杜诗“三吏”“三别”的主题作出新的阐释,认为:“少陵先生诚然是一个反对军阀混战的人,但决不是‘非战’,不仅不‘非战’,且极力主张‘抗战’……‘三吏’‘三别’不单不是‘非战’的作品,而且确是‘抗战’的巨篇!”虽然易君左也难免以当前的思想观念来解释杜甫,但他对“三吏”“三别”的解释更为确切,杜甫这些诗篇所歌咏的是抵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保家卫国的战争,杜甫对这类正义之战是支持的。 (二)汪伪政权下杜甫“非战文学”论调之重启 “利用文艺为‘和平反共建国’的反革命事业服务,是汪伪政权的一贯政策。”汪伪政权重视利用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等传媒散布亲日卖国言论,误导民众。在前期,他们利用汉奸文艺宣扬所谓的“抗战无益”“和平建国”等错误思想来消磨民众的抗战意志。1943年汪伪政权对美、英宣战后,又鼓吹战争。这种汉奸政治思想侵蚀了汪伪政权辖区的古代文学研究。 曾在汪伪时期任江苏博物教员的吴和士,在汪伪刊物《经纶月刊》上发表文章说:“唐诗价值之一种,是鼓吹非战主义。”并感慨:“七七事变,是中日双方很早就积了许多误会的因基,一旦总爆发,所以当时的情势,要避免这次战争,诚然不易,可是遇到光荣的媾和机会,就应该解除误会,言归于好;须知多一日战争,国家多耗一日元气,人民多受一日蕩析流离之苦,若闭目一想前线战争情状,父死于前,子仆于后,一炮轰然,无量数的生命资产,化为灰烬,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亦不可以已乎?所以我们的献身和运,目的不在人,端的是为了国家元气,为了人道主义。”说得冠冕堂皇,但丝毫不能掩盖他卖国投降主义的用心。这时期汪伪政权亲日投降政策在杜诗学上的表现,就是重提杜诗“非战”论,过度阐释杜甫的“非战”思想。1939年创办于上海的《更生》杂志,鼓吹汪精卫的新国民运动,宣扬投降主义。该刊1940年发表黄一鸣《杜甫反战诗歌的研讨》,把“三吏”“三别”通通解释为“非战”诗歌,极力渲染战争的破坏性、残忍性,标举杜甫为中国历史上反战争、爱和平的民族诗人,而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则是由历史隐射现实,他说: 每一念及现今我们国破的情状,真令人不寒而栗,痛恨蒋、共抗战到底的失策,想不到当年杜甫描写战争罪恶的那许多诗,竟是今日中华民国的写真!我们敬爱杜甫的思想和他的诗,便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消弭中日惨酷的战争,向前努力,以期实现我们理想中合于正义的和平,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这是每一个民族志士应负的重责。 抨击当时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才是该文的真正主旨。作者站在被侵略的土地上,面对遭受帝国主义铁骑蹂躏的苦难同胞,不去谴责侵略者的暴行,激发民众抗敌救国的精神和勇气,反而大力渲染战争的残酷无情,鼓吹“消弭中日惨酷的战争”,卖国投降的嘴脸昭然若揭! 日军侵占广州时,曾组织一个叫“协荣印书馆”的出版机构,编辑《华南公论》杂志,鼓吹东亚共荣共存。袁文在该刊著文称杜甫的诗歌“无一不是写当时战争之痛苦”;兆麒编写《石壕吏》短剧,其中说:“这样连绵争战,我想都是世界的末日啊!”在反侵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汪伪政权地区传出这种声音,显然是居心险恶的。 《新东方杂志》是汪伪特工头子苏有德主办的刊物,宣扬“中日亲善”。庄有钺在上面发表《杜甫的非战文学》,哀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过于杜甫的时代,我们人民为战争而所流的血泪,所受的颠沛流离的痛苦,比他那时代的人民,不知要加上多少倍;然而当今在文学上能有多少是代表时代的作品?”这完全是用汪伪政权所谓“和平亲善”的宣传策略来解读杜诗,过分扩大杜诗对于战争灾难性的描写。作者不管战争的性质,以偏概全地阐述杜甫所谓的“非战”思想,有意识地遮蔽杜甫对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支持,以杜甫所谓“非战文学”为对照,斥责当时为民众呼吁和平者能有几人。而他撰著此文的真正目的是“代作我人的借镜,以开辟新的文学园地,统一新的非战文学的阵线”,显然是为汪伪政权的反动政治宣传服务的。 然而,随着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它的宣传策略又作出巨大调整。1943年,根据日本的指令,汪伪政权发表《宣战布告》,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与日本全面合作,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号召沦陷区的人们“从今日起,踏入了保卫东亚的战争了。我们每一个人,要努力做成一个保卫东亚的斗士”。配合这种新的形势,曾经为汪伪政权机关报《中华日报》工作的萧剑青,发表《唐代非战诗人的检讨》和《杜甫非战思想的再检讨》等文,在前文中他说:“非战在某一种环境中,是错误的……在种族被压迫至不能喘息的时候,我们为要求得生存与自主,就要自己结合起来,向那侵略的野心者作最后一兵的战斗,俾得‘死里求生’的达到。中国古谚有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存’便是这个意思。”他辨析25位唐代诗人的“非战”作品,均给予激烈抨击,最后的结论是:“唐代所有非战的诗人,思想全是谬误的,他们不应该写出那些煽动逃军或分散军心的文字。”他们应该多多地替政府写出雄壮热烈的铁血主义的作品,来感动民众鼓励民众,一致去赴难!在《杜甫非战思想的再检讨》一文里,萧剑青提出“非战误国”,据此而批评杜甫,“唐诗人中以文艺论,杜工部当属第一;但以贪生怕死,宣扬‘非战’而论,杜工部亦属第一”! 如果脱离了历史背景去阅读这些文章,你会产生萧剑青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错觉。萧剑青在文中很明白地交代:“当二年前,国民政府参战,向英美发动攻势的消息,传入我的耳鼓的时候,我正在整理这《唐代非战诗人的检讨》一文,我认为唐代非战诗人的思想是谬误的……目前,是需要发挥拥战文艺的时期!东方民族的文化份子联合起来!”他所谓的“国民政府参战”,就是指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他所谓的“东方民族”,就是指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所以萧剑青的这两篇文章完全是“应时”奉命之作,是为配合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而作的。他不惜歪曲历史,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代爱国“非战”诗人作出如此苛刻、粗暴的抨击,对杜甫作出不恰当的贬抑。其实,杜甫既有一些非难不义战争的诗篇,如《兵车行》反对穷兵黩武地扩张领土,也有不少支持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作品,如“三吏”“三别”与后面所举的《甘林》等,并非如萧剑青所说,是第一贪生怕死之人。他的荒谬结论,反过来暴露了“遵命”式的学术研究存在多么大的盲点和误判。 (三)延安红色政权影响下的杜甫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红色政权非常重视思想宣传、文化建设和精神鼓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指引下,延安文艺界和各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并受其影响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文艺”,进行积极的精神动员,统一民众意识,坚定抗战意志。缘此,古代文史中抗敌救国故事和爱国主义精神得到挖掘和发扬。如郑振铎于1939年以“源新”笔名在《鲁迅风》上连载“民族文话”;郭沫若不仅创作了历史剧《屈原》,还发表了近十篇研究屈原的论文。这些都是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当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杜诗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也为进步的革命的文人所重视。桂涛声192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投身抗日宣传。1939年,他在河南巩县拜谒杜甫墓,发表《杜甫墓上》,激切地呼号: 桂涛声青年照 起来吧诗人!起来吧杜甫!我们的国家危险极了,我们的民族危险极了,我们正需要你伟大的民族诗人来号召群众保卫祖国。起来吧诗人!起来吧杜甫!啼饥号寒的人太多了,流亡他乡的难民太多了,我们正需要你伟大诗人的同情来安慰他们,组织他们!起来吧诗人!起来吧杜甫!背叛民族的汉奸越来越无耻了,醉生梦死的人们越来越多了。我们正需要你伟大刚方的笔来批判他们,来刺破那汉奸丑恶者的脸谱!” 同样是以文学的方式演绎杜甫,此文与前面所提在“非战”声浪中出现的《石壕吏》小说、戏剧不同,作者着力发掘杜甫积极有为、振奋人心的抗争精神,而不是一味地哀怜、悲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需要杜甫诗歌来安慰,更需要从杜诗中汲取奋勇斗争的力量。抗战时期的爱国文人把抗战精神注入杜诗之中,借杜诗来抒写抗战情怀,实现了视界的融合。杨子固就说:“我们的老杜,好像对我们太多情了,他歌着我们胜利以前,他又在歌咏着我们胜利以后,而且他那笔触的沉著有力,总在激荡着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 当时一般论者阐述杜甫战争观时,多列举“三吏”“三别”、《兵车行》《哀王孙》等诗篇,黄芝冈则另辟蹊径,依据杜甫的《甘林》诗来阐论“国民义务”。《甘林》诗曰: 舍舟越西冈,入林解我衣。青刍适马性,好鸟知人归。晨光映远岫,夕露见日晞。迟暮少寝食,清旷喜荆扉。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试问甘藜藿,未肯羡轻肥。喧静不同科,出处各天机。勿矜朱门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 大历二年吐蕃寇近畿,郭子仪屯泾阳,京师戒严。诗中的里老向杜甫诉说因负担战时重税已没有饱饭吃了,辛辛苦苦种的豆子也都充作赋税供军队用了。黄芝冈分析说:“杜甫‘屈指数贼围’是答问也是安慰,但劝他‘死王命’‘莫逃亡’,却正告里老以国民义务。至今读两千年前的诗更感到词严义正,杜甫真不可及了。”杜甫虽然同情邻老,但对这场驱逐侵略者的战争,是支持的;故而末四句答邻老,“勖以急公之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履行战时的国民义务。 翦伯赞于1937年5月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在重庆从事文化工作。1944年,他在中共于重庆出版的理论刊物《群众》杂志发表了长文《杜甫研究》。文中,翦伯赞以唯物史观和阶级论观点阐述杜甫的时代、身世、性格和作品,称赞杜甫具有“反抗强暴,鄙视权贵,同情穷人,痛恨贪官污吏”的性格,他的作品“揭露社会的黑暗,控诉权贵的罪恶,谴责贪污剥削”,具有“写实主义”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翦伯赞讨论了杜甫的战争诗,说:“为了讨伐安史,唐代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的进行中,捕捉壮丁,征发粮草,弄得民不聊生。”并列举了《石壕吏》《新安吏》《垂老别》《无家别》《新婚别》等诗加以说明,但是在发表时国民党的文化审查官把这些诗篇通通删去。这一手段正暴露出国民党当局对于杜诗“非战”还是“抗战”还存在着依违的态度。 而延安解放区则把杜甫视为苦难人民的代言人,认为杜诗写出了被压迫阶级的呼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1946年曾写信指示:“边区应该对中国的最大诗人杜甫有所纪念。”恰好延安城南外杜甫川口有唐左拾遗杜公祠,陕甘宁边区政府拟把杜祠修葺一下,次年诗人节开一纪念会。同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的钱来苏发表《关于杜甫》,称赞杜甫“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骨头的一个人……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一面是强暴的帝国主义,一面是极无耻的汉奸群,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像杜老这样有民族气节、有骨头、富正义感、而又是非分明的人。做诗的朋友们,要学习杜老,把复兴民族的义愤和勇气,以新的形式,歌唱到广大人民中去”。 1937年9月,同济大学教授冯至随校内迁,年末抵达赣州。冯至作《赣中绝句四首》,其二曰:“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至晚年,他的《自谴》诗依然回忆说:“壮岁流离爱少陵。”抵达昆明后,冯至转入西南联大外语系,与闻一多、朱自清等民主进步人士多有交往,对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和进步学生表示愤慨和抗议,思想愈益进步。1946年后,他发表了多篇研究杜甫的论文,至1952年出版了《杜甫传》。冯至研究杜甫,是把自己在战乱频仍中的感受与杜甫漂泊西南的生活联系起来,强调杜甫在乱世中的执著精神,崇仰杜甫是“爱人民爱国家的诗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矛盾的性质在不断改变,通过不断地重新阐发,杜甫最终以“爱人民爱国家的诗人”的形象进入了新的文化视野。 结语 中国传统的文史学术历来具有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双重追求,前者力求还原研究对象的真实存在,后者追求学术的当下价值和意义、应对现实提出的问题,二者并非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而是相互补充、相互矫正,各有偏向而又构成张力。 本文作者周兴陆老师 杜甫是一位将儒家“淑世”情怀发挥至极的诗人,杜诗被誉为“诗史”。后世每当兵革兴起、世运危难、生灵涂炭之时,杜诗研究就活跃起来,人们感同身受,从杜诗中获得同情和慰藉,得到信心和勇气的鼓舞。正如北宋爱国将领李纲所言:“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羇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时平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辞如生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遭遇兵火丧乱,人们多是杜诗的知音。通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杜诗又一次走进人们的心田,安慰和鼓舞人心。现代杜诗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学术研究参与了时代思想的言说,显示出生命活力。但是不同时期,战争的性质各有不同;同样是抗日战争,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对战争的认识态度,也互有不同,甚至同一政治势力的战争态度前后还发生变化。他们都借助杜诗研究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观念,把自己的战争理念贯彻在杜诗的阐释和评论中,借以左右舆论,引导民众。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学术史时,不能笼统地评论杜甫“非战”说,须要进一步探究言说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动机和社会效果,进行具体的剖析。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虽然杜甫的战争诗不再是一个研究的热点,但时代向人文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须要做出回答。人文研究的“淑世”情怀,同样不能迷失。 原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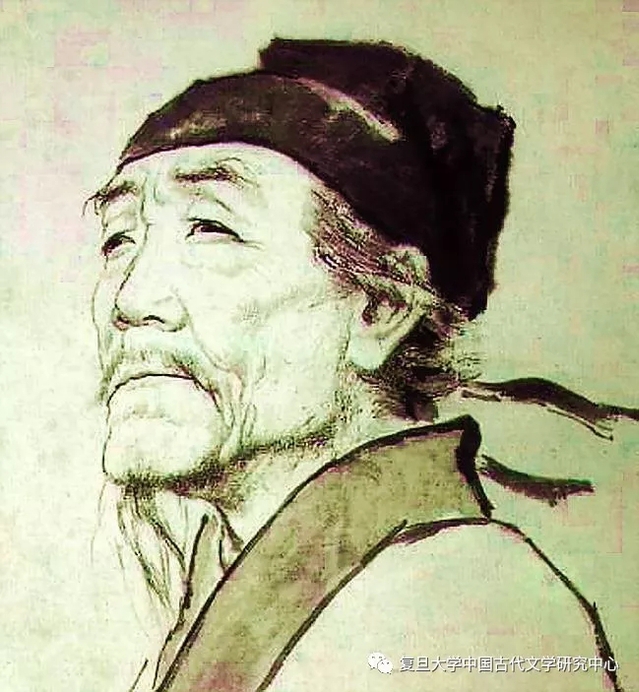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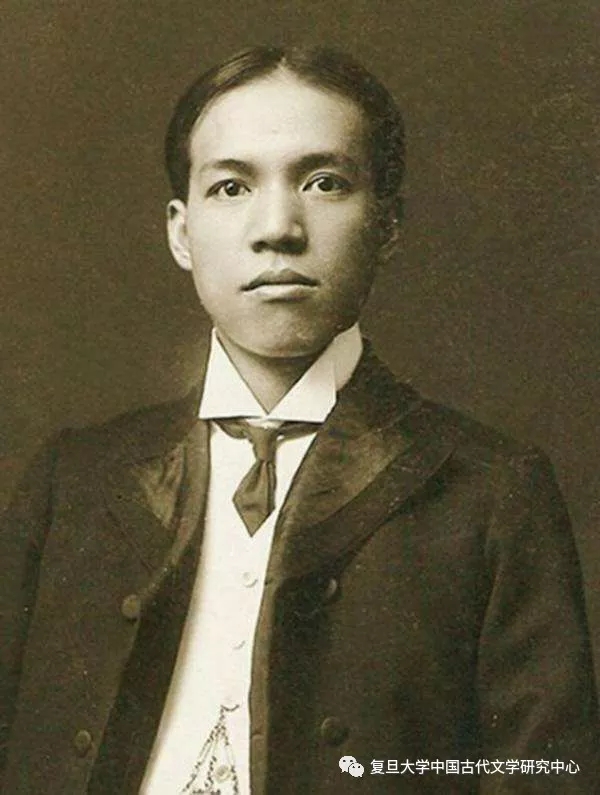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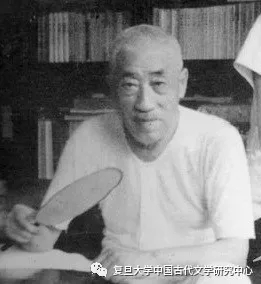


|
|
|
|
|
|
|
|
|
|
Copyright © 2013 |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电话:021-65643670 邮编:200433
| 历史访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