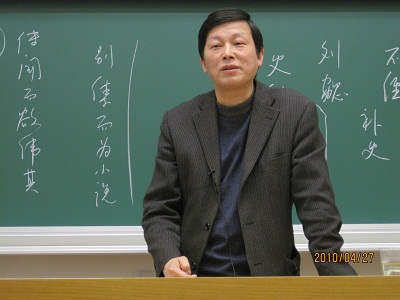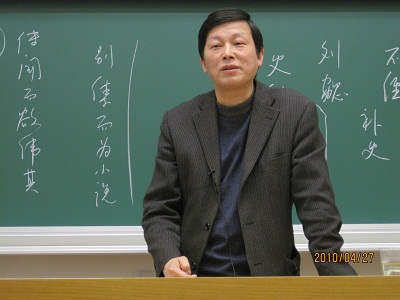
2010年4月27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0中国古代文论讲座”第十四期邀请到了长江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副会长谭帆教授,做了题为“‘小说’与‘演义’——兼谈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术语研究的相关问题”的讲座。黄霖教授主持该讲座。
谭教授在讲座开始之际首先向大家阐明了他的总体思路,将本次讲座主要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小说”语词内涵的阐释;第二部分为对“演义”语词内涵的阐释;而第三部分则为明晰“小说”与“演义”之间的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术语的价值所在。
谭教授首先梳理了“小说”这一语词概念发展的四个时期。由于“小说”在中国古代所指称的对象是一个庞大的门类,所以对它的定性最初就是一个文类概念,而非文体概念。“小说”语词内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始于先秦时期,以《庄子·外物篇》和《汉书·艺文志》为代表。这时的小说是“小道”,是与“大达”相对的浅薄之说,无关于政教。通常认为小说来自于民间,其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因此,这一时期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就是确认了小说文类,明确了小说的基本范围,以及确认了小说呈贬义的基本观念价值。第二阶段约始于南朝,以“殷芸小说”为代表,认为小说是“野史”,是“传说”,有别于“正史”。梁武帝命殷芸将选编通史时所馀之大批略为荒诞或流于传说的史料“别集而为小说”。这一语词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具有了新的内涵。另外,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出现了分流,杂史、杂传大量出现。史学家们认为这种书的价值不能与正史同日而语,因此要将其分流出“史传”的主体。所以,这一时期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就是直接地促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乃“史之馀”的观念,它奠定了中国小说重要的价值功能,即“补史”。第三阶段约始于三国时期,以《三国志·魏志》等诸多文献记载为代表,“小说”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伎艺”的概念。从南朝时的民间伎艺发展到唐代时成为一种专门伎艺,再到南北宋时期“勾栏”、“瓦肆”中“说话”表演的盛行,小说逐渐从一种口头艺术演变为“说话”所用底本的文本,即“小说家话本”。第四阶段约始于明清时期,以《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四大奇书”为代表。这一时期通俗小说的兴起极为繁盛,最终确立了小说作为“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的概念。从“小说”这一语词演变的历史过程看,它既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其演化主要表现为它所指称对象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更替。因此,对于“小说”这一语词的研究应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而非机械生冷地截取片段的语义。
在讲述“演义”语义的界定时,谭教授首先纠正了大家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即演义就是历史小说。其实“演义”在历史上是小说的文体概念,即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文体,包括话本体和章回体。章太炎先生在《洪秀全演义·序》中指出,演义有两大类,一为演言,一为演事。演言即是对义理的阐释,演事则是将历史通俗化。《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对“演事”最生动直观的例子。演事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的变文,不过当时多称为“变”、“话本”,至宋代多称为“讲史”、“演史”等。而其作品最早以“演义”为名称的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以“演义”的特性可归纳概括如下:一是在于其通俗性;二是在于其风教性,也就是用通俗的形式来完成经书史传无法实现的,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始,其后所有通俗化的作品都称之为“演义”。
最后,谭教授还梳理了小说与演义之间的关系,即小说早于演义而出现,其指称范围包括文人笔记、通俗小说两大类。演义是通俗小说的专称。小说的概念可以包含演义,而反之则不可。二者在指称通俗小说的范围内是可以重合的、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