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高峰,不仅数量骤繁,而且呈现较为明显的范式转换。当时的文学史家即有以民国八、九年划界的,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的开端。如黎锦熙的《国语文学史》“代序”,在阐述教育部颁示正名后的“国语”之于国语文学史进入“正轨”的意义之同时,认为“民九这年要算是开一新纪元了”;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概要》第一章“绪论”中则指出:“到了民国八年以后,中国的文学界才发生变化,把原有的谬见打破了。从此以后出版的文学史,已把界限划清,可算是进了一步。”当然,二人观察、论述问题的立足点不尽相同,前者承胡适1918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十字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更着重强调“言文一致”的实现之于文学革命的意义,新的文学史在此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后者虽亦指出文学界的观念变化带动文学史研究的重新界定,关注的重点主要在文学史自身的构建。 这一划界本身,其实已经说明这样一个高峰以及所伴随的新一轮的文学史转型何以会出现,我们对于中国纯文学史兴起的探究,自亦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的开展溯起。这当中,当然不能不表彰胡适之于文学史建设的贡献,无论是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主张,还是他的文学史实践,都显示了一种现代学术立场的确立。简言之,这样的立场可归结为如下诸要素: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进化论史观以及新的文学价值观念,而与传统的史学、文学观念划出决裂的沟壑。毫无疑问,它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人们构建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盘,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胡适照片 不过,就胡适的文学史思想与研究本身而言,并不必然导致文学史的构建向纯文学史方向发展,相反,还常常成为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文学史研究者批评、超越的对象。由胡适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式提出的文学标准——“言之有物”,谓“吾所谓‘物’,约有二事”,即“情感”与“思想”,不能说没有接受西方浪漫主义以来新的文学观念,然而因为这种新的“以质救文胜之敝”说,是基于过去的文字形式“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这样的想法,换言之,乃将文字形式看作是表现情感与思想的工具,故而提倡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文学自身的定位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梅光迪、任鸿隽等人提出“文学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的批评,应即针对于此。即如陈独秀亦曾意识到这种“言之有物”论的危险:“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认为作为一种美术的文学,应是具独立价值的实体,而非仅仅依附他物的工具。这种超功利的文学观,是如王国维先已接受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美学的观念,有人因而将王国维与胡适的主张相比照,指出胡氏“虽以白话文学相号召,而实则其目光专注于实用之方面而无暇及于美术也,专注于语言之方面而无暇及于文学也”。毋宁说,在对文学功用的认识上,胡适延续了梁启超文化启蒙的路径,其实际关注的指向往往落在文学之外,以致全然以文化革命的目标替代文学自身的目标。因此,当他的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白话文学史》刊行不久,就有人提出颇为中肯的批评:“胡先生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带上了这副着色的观察眼镜,所以结果文学史上时代的重心,是失其均衡了,体制的演变,是模糊不清了,而且生出种种偏见武断的结论出来。”后来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更指出其症结所在: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乃舍文学的本质上的发展,而追逐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那个狭窄异常的一方面的发展之后,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只是“白话文学”的发展。执持着这样的“魔障”,难怪他不得不舍弃了许多不是用白话写的伟大的作品,而只是在“发掘”着许多不太重要的古典著作。 郑振铎照片 显然,为文学史提出新的历史学方法与任务的胡适,并没有着意解决文学史的另一重要前提——什么是文学,虽于1917年6月自美归国前,通过阅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时代》(Renaissance)等,稍有系统地找到欧洲各国国语文学发展的公例以为援据,显示了其留学期间已有的世界文学视域,然这种文学观念的进展,恐怕还有待于新一轮西方文学论的学理输入,尤其是西方文艺学或文学理论学科的兴起与传播。 无论如何,胡适所指示的方向以及他所存在的问题本身,皆体现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学建设所面临的真实语境,纯文学史的兴起,亦由此触发,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实现其在文学史对象与机能等诸多方面更化的作用。 在整理国故的目标下 谁都不会否认,中国文学史学术体系进入一个相对自觉的发展阶段,其更为近且的动因或背景,应与“整理国故”思潮密切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已经有学者对近来日趋发展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进行过即时的总结,划分出若干阶段:首先概述“新史学的发达与史观的改变”,是文学史转型的契机,强调“一直到中西文化发生交流以后,在《天演论》等书译出以后,中国思想界才有进化的史观,才渐渐地把目光转移到客观的历史发展的状态上去”;其次是“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法”,具体指“在观念初改变的当儿,只是形式上的转移,在本质上还是过去的骸骨”,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便是这样的代表作;再次是“五四时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法”,指出“文学革命以后,国故整理派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便大大地进了一步。他们已从本质上接受了工业国家进化的史观,并接受了科学的方法,要把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遗产,重新评价”,着重阐述的便是胡适《白话文学史》的示范效应及其拓展的疆界;最后则指示“今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趋向”,认为“现在是需要阐明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消灭底社会根源了”,那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下的社会学研究新方法。这是尚处身于方兴未艾的新的文学史建构潮流中的回顾与展望,现在看来,其把握在大的方向上仍显示了相当的准确性,国故整理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已获得比较充分的体认。 由上述胡适的观念与立场来看,至少在他身上,发起“整理国故”运动,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阶段。在他于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中,借着对“新思潮的精神”的阐释,认为其“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而“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为此,在总结过去两三年新思潮运动于“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两项手段之经验的同时,指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号召人们“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从其以“再造文明”为新思潮唯一目的来看,这一“整理国故的工夫”,实是新文化运动实现由破而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至于具体的整理方法,一仍其“历史的”眼光,即“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在他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又条理化为三个方向的研究方针: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作为现代学术立场最为清晰的表述,这其实是将之同条共贯、相互依援的内在关系予以分解,比较的研究,因欧美日本学术界的参照,而赋予整理国故科学的方法与新的价值观念;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与新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可以对我国历史上原来漫无统序的各领域学术作系统的整理,一方面又可突破传统视域的制限,以全新的文化史观,发掘、扩大研究的范围:“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而要实现这种国学的系统的研究,须先从事“专史式的整理”,“文艺史”即在其列。于是,身为这样一种专史的中国文学史,就从清末民初临时用作大、中学堂教材的最初之国别文学史外在形态的嫁接拓展开来,有了某种自觉建构与范式更新的要求;虽然最先由革新的史学观念突入,但因为有新的方法相支撑,又包含价值评判这一要素的存在,加上“专史式的整理”的部署,这样的研究诉求很自然成为通向作为方法的文学史、对象的文学史的桥梁,胡适自己的《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也正是这一学术风潮的产物。 说“整理国故”是一种思潮、一种运动,并非有夸大其声势或作用之想,相反,它在当时的影响仍值得进一步阐发。如果说,上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集中体现了以北大为中心的倡导者于该项事业自觉的纲领、计划,那么,围绕着这样的纲领、计划,他们不仅身体力行,积极开展研究,并且借助现代传媒及传播方式,交通声气,广为宣传。如胡适其间在南北各大学巡回演讲,反复申示科学方法及整理国故的主张;而如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2号“国内文坛信息”专栏发布有关中国文学研究近年来已渐流行的最新动态说:“在北京方面,《努力周刊》及北京大学所出《国学季刊》都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出来。在上海方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及本报,也都很努力于此。”亦可见这一思潮的传播速度及所收到的成效。更为重要的是,依照“整理国故”的设想,还建立起了现代学术体制,使之成为组织实施上述计划并培养新生学术力量的可持续发展阵地,并因此有了细密的专业分工。如所周知,成立于1922年2月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即是在国际学术界刺激下,承载新老有识之士整理国故理想的现代学术机构,由其组织系统观之,具有多种学术功能。在其示范下,其他各大学亦纷纷成立类似的国学研究机构,在南方具有代表性的,即为1924年成立的东南大学国学院,尽管其宗旨、发展方向未必相同。有鉴于此,我们发现,这种现代学术机构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建设,包括朝着纯文学史方向的发展,存在着相当大的制度效应,二三十年代涌现的那些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很大一部分即出自此南北两大国学研究重镇。此外当然还有以京沪两地为首的全国各大城市的其他研究者,那是因为当时京沪两地的报刊经常刊载国学门的消息,而诸如《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等在全国各大城市发行,产生即时而有效的广泛影响,可以说在“整理国故”思潮的推助下,一个各区域共享的现代学术社会正在形成。 就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而言,如1931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中国文学流变史》的郑宾于,即为“风俗调查会”与“歌谣研究会”成员,曾积极参与新的民俗学方向的文学研究,于1925年至1926年在《国学门周刊》上已发表不少相关论文;1935年由北平著者书店出版《中国纯文学史纲》的刘经庵,虽就学于燕京大学,然与容肇祖等于“歌谣研究会”成立之初即加入成为会员,著有《歌谣与妇女》等作;而容肇祖于1922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即从张竞生组织“风俗调查会”,并与顾颉刚等从事风俗调查活动,曾在北大的《歌谣》周刊、《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等发表相关论文,后任教厦门、广州及北平等地大学,亦曾著《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5年初版)。至于先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学习的冯沅君、金受申、林之棠等,皆各有其文学史著述,分别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海大江书铺1931年初版)、《中国文学史简编》(大江书铺1932年初版)、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上(文化学社1933年初版)、林之棠《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北平盛华书局1934年初版)。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可以说,正是“整理国故”目标下的现代学术体制培养的新一代成果,从下面将要论及他们相关著述所体现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来看,显示了新一轮运用西学方法及学科体系整理、研究传统学术的整体推进。他们中如林之棠,在其《中国文学史》“叙例”中,就曾叙及在北大读书期间已开始文学史的写作。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再版“自序”中,也以自我批判的笔调,记述了他们早年接受的影响来源:“这书初稿是在一九二五—三〇年间写成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受了五四运动右翼的‘整理国故’的影响……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植过来。”其他如1927年先后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罗根泽,也是在研究院学习时,就开始着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后接替郭绍虞到清华大学任教,更全力转到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1929年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张长弓,师从郭绍虞专攻中国文学史,著有《中国文学史新编》(开明书店1935年9月初版),申明采用的态度是“就现代文学观念下,去寻绎擘画前代的史料,以见其史的流变”。 1924年9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 从东南大学国学院负责人顾实草拟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我们可以看到该院的成立,是同一风潮的产物。顾实本人有《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不管当时所受评价如何褒贬不一;1921-1924年主持东南大学国文系的陈中凡,本身是北大出身,1923年主编东南大、南高师合办之《国学丛刊》,同样力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是我国该领域最早的著作;由陈中凡举荐的继任国文系主任胡小石,亦曾有作为大学教科丛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上海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1930年初版),至今获得很好的评价。其他像1922年应陈中凡之聘重返南京的吴梅,原在北大即有《中国文学史》讲义,后又著《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他在东南大的学生卢前,不仅有《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这样承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而作的断代分体文学史著作,也有《何谓文学》(大东书局1930年初版)一类“文学概论”讲义,显示这个时代培养的学者关注的领域与新的视野。 在现代文化中心的上海,新文学及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亦非常显著。前举郑振铎说到上海方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及《小说月报》在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上努力,与北京方面构成南北呼应,便是例证,尽管不同派别之间有纷争。为此,汪馥泉还曾在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上发出《“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为自古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模像样的《中国文学史》,建议包括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在内的诸文学团体中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打破文学上的派别来共同从事”,并据研究对象构设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分组表,认为此项修撰事业若能成功,还将“改变从前的文学观念”和发生“新意义的考据运动”。郑振铎于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后,即针对有人提出的提倡国故是加于新文学的一种反动,在该刊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并撰《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予以阐述,认定整理国故是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他们的整理研究工作,也正是在“白话文学”所显现的新的文学价值观念之延长线上着手展开的。郑振铎自己自不必说,当另撰文论述,沈雁冰也是一方面从事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著《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予以介绍(见其与刘贞晦合编《中国文学变迁史》,新文学研究会1921年初版),一方面则关注中国寓言、中国神话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小史》(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出版)、《中国文学史新编》(北新书局1936年初版)等的赵景深,一直致力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研究。其他如著有《中国文学史大纲》(光明书局1925年初版)、《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初版)的谭正璧,也受到郑振铎的影响而致力于南戏、话本小说、弹词等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史略》(梁溪图书馆1924年初版)、《中国文学史概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的胡怀琛,虽曾被五四新文化一派斥为“旧派文人”,然实际上不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29初版)、《中国寓言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中国民歌研究》(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系列,而且早先还曾撰述《新文学浅说》(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初版)。 整理国故运动从一种思潮的狂飙突进,发展至现代学术社会的形成,其间的环节与构成当然十分复杂,无论附和或是反对的意见,都有各种势力及立场的诉求。但是,作为主流的主张,以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在指示现代学术方向与任务的同时,已经随着运动的开展,全面推进至实践层面,运用西学方法及学科体系加深学术的本土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在这样一种中国文化史或国学研究日趋科学化、专业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学史研究于新文学运动已经提出的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不仅有更强烈的专门对象、范围及职能等鉴定的自觉要求,令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有所落实,而且因这样的意识,使得胡适的“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成为某种共识,如前举郑振铎、沈雁冰的看法,而令西方新兴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有植入的空间,这恰恰是成就中国文学史体系向纯文学史方向发展的一个契机。 新一轮西方文学论的引入 回溯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文学史学术体系的建立,还不仅在于史学立场与方法的更新,更有赖于以新的文学观念为核心,构成对文学自身一种系统性的认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社会,无论是文学批评朝着囊括整个文学研究的方向发展,取代诗学和修辞学,还是像在德国那样接受“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的术语,作为一种新的诗学和文学批评的口号,都显示了文学自身的学问,在与美学分离之后,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术研究学科。这种学术性文学研究,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随着其自身的发展,逐步被引入中国学界,通过强调文学特质及审美价值的文学原理,在推进中国纯文学史建构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晚清以来,有关“纯文学”的观念,已经日本的中介影响而输入,并且正经历着由美学命题向文学论命题的转化。从王国维1905年发表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鲁迅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到周作人1908年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黄人1911年编纂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中有关“文学”的词条,我们已可看到这一现象及其递变,虽然那或许仅体现个别先锋学者在观念上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却开启了我国文学领域由传统向现代历史性转换的路径。与此同时,《文学概论》样式的西方文学论,亦已经日本的中介影响传入,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从上引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黄人《中国文学史》第四编《分论》第一章第一节有关“文学”定义的讨论,以及吕思勉《小说丛话》等,至少已可比较集中地看到对日本英国文学研究者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纳;之后如鲁迅1913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朱希祖1919年发表的《文学论》等,也仍可看到太田氏《文学概论》的影响;至于伦达如1921年出版的《文学概论》,实即为太田氏《文学概论》的编译。但是,一方面,太田氏《文学概论》引入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中,维多利亚时代那些批评家的思想观念其实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唯美主义运动以来的文学批评及观念的全面译介,尚有待于像本间久雄、厨川白村这样的文学理论研究者的投入;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在伦叙《文学概论》出现之前,亦主要在各自关注的领域接受、运用该著介绍的相关观念,而非整个理论体系。从文学史的应用来看,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虽在有关文学定义的讨论中长篇译介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相关论述,却仍不能说在整个文学史叙述中有很好的贯彻;朱希祖的《文学论》,亦曾引用太田氏的“纯文学”之说,但那仅仅在他1920年刊行《中国文学史要略》重新检讨自己的立场时发挥了作用,即让他认识到自己这部文学略史仍非基于新的文学观念作成。 这种被西方学者认为具有某种延迟性(belatedness)特点的受容,至五四新文学及整理国故运动以来,才有所改观,而有了较为迅猛的发展势头。正是基于胡适奠立的现代学术立场,学界有了更为自觉的“输入学理”的要求,其接受西学影响也有了更为直接的渠道,当然,以日本为中介的渠道仍继续存在,无论传入的学说之众与更替的速度之快,皆非昔日可比。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伴随学科体制的进一步更新,“文学概论”课程在国文学科目中的确立并展开,不仅使人们得以对西方生成的诸多文学理论及其来龙去脉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而且意味着对于传统中学壁垒的进一步瓦解。而在这一阶段,大量西方文学论被译介过来,并被予以不同程度的消化、整理,正是在这种学科更新的前提下所发生的效应。作为这种译介新的西方文学论重要形式的各种《文学概论》著作的骤然涌现,便是其突出的表现,当然其间各有其不同的来源与构建。学科体制下文学理论的独立与骤兴,除了令新一轮西方文学论的引入有即时、持续、有效的机制与渠道,全面普及新的文学观念与知识,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或许是,自此在比较的视野下,被纳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相辅相成的格局,从下面的分析将可看到,它对于中国文学史体系的更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创生与发展,作用是相当显著的。 其次,是各文学团体、研究力量有意识地竞相开展相对系统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及观念的译介工作,显示正在形成的现代学术社会的某种共同追求。如“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的北大新潮社,其骨干罗家伦在《新潮》1卷2号发表《什么是文学?》,即据英国百科全书“文学”之定义,征引包括Brooke、Mathew Arnold、Hudson、Possnett、Hunt等在内的15家说法。在东南大学,景昌极、钱堃新在梅光迪、吴宓的影响下,翻译了美国学者温彻斯特(C. T.Winchester)的《文学批评之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梅光迪校),先是在《文哲学报》1922年第2期开始刊登第一章,刘文翮《介绍文学评论之原理》有述评(《文哲学报》1922年第3期)。又如少年中国学会的黄仲苏(曾任教于东南大学),在《少年中国》第9期至12期(1924),已将朗宋《法兰西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概略》与《文学史方法》译出。而在上海,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为中心,在介绍外国文艺及理论方面的成绩最著。《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1921年8月)曾刊出《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的预告,其中就有拟定为郑振铎译的莫尔顿(R.G.Moulton)《文学的近代研究》,拟定为沈泽民译的亨德(T.W.Hunt)《文学的原理与问题》,以及拟定为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合译的蒲克(G.Buck)《文学之社会的批评》等。1923年1月,郑振铎专门撰写了《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一共介绍了包括托尔斯泰《艺术论》、波桑鸠《美学史》、穆勒《文学的研究》、蒲克《社会的文学批评论》、韩德生《文学研究导言》、韩德《文学的原理与问题》、穆尔顿《文学之近代研究》、柏斯奈特《比较文学》、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等五十部书,体现其“我们应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的想法。这些著作亦基本上在二三十年代先后被翻译过来,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又曾与郑振铎同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并与郑氏一起主编大型月刊《文学》的傅东华,在译介美国最新文学原理著作上尤为著力。至于创造社成员,因其留学日本的背景,仍以日本为中介,在大力翻译欧洲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到唯美主义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将相关文学理论著作译介过来。除了像郁达夫《文学概说》、田汉《文学概论》这样主要传播厨川白村、本间久雄等的文学论,还有如张资平曾译有藤森成吉的《文学新论》(上海现代书局1928),以及斋藤勇《以思潮为中心之英文学史》(《学艺》第9卷第1期,1928)这样的文学史论。 尽管在这个时代新一轮“输入学理”的风潮下,包括西方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种文学思想与观念以一种共时形态适时涌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然从当时专门从事或关注西方文学批评的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在我国学界影响比较大的近代西方文学论著作,还是相对有所集中。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宗旨身体力行的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胡愈之,在试图清理西方文学批评之意义、方法,为研究新文学的人们提供某种借鉴时,曾有如下叙述: 文学批评在西洋差不多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要把他的意义、历史、派别详细研究,自然不是几千个字所能尽的。现在暂且参考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Moulton’s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黑德生的《文学研究导言》(Hudson’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韩德的《文学的原则和问题》(Hunt’s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andProblems )和别几部书做了这篇,权作在我国介绍文学批评的引子罢。 在其下的具体概念论析中亦显示,这几部被认为代表最近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著作,确成为他立论的依据与资源。稍后,有留美经历,并曾选修过白璧德《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的梁实秋,则因此提出对近时文艺理论界的批评,曰: 试举西洋文学批评杰作之为我国人士所熟悉者,实在寥寥无几,恐怕除了一部何德孙的《文学入门》,穆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文柴思特的《文学批评原理》以外,十分之九的西洋批评杰作,在我们中国是一个未曾发见的宝藏。 可以说从反面表明这些论著在中国的传播。 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学论的作者,皆为世纪之交美国的学院派学者,既从一个侧面展现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独立的科目在西方大学讲坛上如何被传授、被推进,亦可由此窥见这个时代的中国学界受自美国的与日俱增之影响力。其中如温彻斯特(Caleb Thomas Winchester,1847-1920)(又译作“文齐斯德”或“文柴思特”),是美国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英国文学教授,所著《文学批评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出版最早,为美国The Macmillan company1899年初版。该著的引入,系梅光迪于1920年在南高师暑期班讲授“文学概论”课程,以之为教材,故又影响景昌极、钱堃新将之翻译出来;不过,差不多与之同时,郑振铎在其主编的《学灯》上,亦已分六次连载了他译述的该著(1921年8月16日至22日);另外,广东高等师范毕业的余心一在《潮州留省学会年刊》1923年第1期上,也译出了该著《什么是文学》一章。韩德(Theodore W. Hunt,1844-1930)(又译作“宏德”、“亨德”或“汉特”),普林斯顿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所著《文学的原则和问题》(Literature,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出版时间亦比较早,为纽约Funk & Wagnalls company1906年初版,故如周作人1908年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已通过日本的接受渠道,引用了其有关“文学”的定义;罗家伦1919年发表的《什么是文学?》视其对“文学”的定义为“含蓄最深各面俱全的一条极好的文章界说”;该著的中文全译,则由傅东华在1935年完成并出版。黑德生(William Henry Hudson,1862-1918)(又译作“何德孙”、“哈德逊”或“赫特生”),斯坦福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所著《文学研究导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George G. Harrap Co LTD1910年初版,该著于1930年,由尚在上海大学英文系学习的宋桂煌全文译出,题为《文学研究法》,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莫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1849-1924)(又译作“穆尔顿”或“摩尔顿”),芝加哥大學文学理论与翻译教授,所著《文学之近代研究》(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15年初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已有《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之介绍,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第17、18卷上连载所译该著的前七章。 即便如此,这个时期来自日本的中介影响仍不可忽视,即就与上述这些近代西方文学论的译介相关的来源而言,如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著作在中国传播之盛,在当时恐无出其右者。本间久雄在就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讲师的前一年,出版了《新文学概论》(新潮社1917年初版),据其撰于大正6年(1917)10月“序”,该著前编“文学通论”部分的说明理路,即依据Hunt的Literature,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Knowlson的How to Study English Literature等著;后编“文学批评论”则主要依据Gayley & Scott的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History of Criticism, 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等著(卷首,第2-3页)。1919年,商务印书馆的章锡琛已以文言译出此《新文学概论》的前编部分,分章刊登于1920年的《新中国》杂志上;1924年,又以白话将后编译出,刊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杂志;合编本于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著另有汪馥泉译本(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1926年,本间久雄以《文学概论》为名出版《新文学概论》修订本(东京堂书店),除加入“文学各论”一编外,有较大增删,厘为四编;故1930年章锡琛又据此重新译出(上海开明书店)。此外,1928年,沈端先翻译出版了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开明书店);1932年,李自珍译出其《文学研究法》(北平星云堂)。据相关统计,仅在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著作重版再版就高达12版次;而此间不少学者接受上述西方近代文学论的思想观念,包括像田汉《文学概论》、郁达夫《文学概说》、赵景深《文学概论讲话》等,就间接取自该著。 上述这些最新西方文学论的传入(包括从本间久雄《文学概论》一类的著作间接引入),对于中国文学史建构及发展所造成的重要影响,同样可以从下面举述的诸多体现纯文学史倾向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得到证实,那些著作的序说在讨论“文学”、“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定义时,往往援引上述论者的观点以为准则,并加以阐发,整个叙述构架亦因此而有所变化,显示他们的学说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已成为一种一般知识,而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获得较为普遍的接受与运用,当然,理解的程度各有深浅。这从三十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学者有意识对中国文学史走过的道路进行回顾的论述中亦可看到,如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时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文史系教授的何爵三,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个根本问题的商讨》一文中就曾总结说,“关于‘文学是什么’与‘文学与哲学科学如何区别’的问题,经过全世界文学研究家长时间的钻研,商讨,现已有相当的结论”,对于马修安诺德、章太炎之说,“像这样广泛的文学界说,人们已不甚同意,而大多数赞成韩德的意见”。他将之归结为四要素:“更明白地说起来,文学是具有想象,感情,思想,和佳妙的外形的。”从本间久雄《文学概论》有关“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特质”等论中已做出的分析、解说可见,这其实是综合韩德、黑德生与温彻斯特的观点而成的。至于他又进而指出“它和 ‘科学’‘哲学’等根本不同之点有四:一、文学自身具有永久的兴趣;二、文学是主观的,有个别性的;三、文学是有普遍性的;四、文学是最能感人的”,则基本上是依据温彻斯特的说法。显然,当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借助这样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学本论及各论,形成相对清晰、完整的新的文学观念与原则体系,就可以在原本芜杂的传统文学事象中,尝试判定属于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并建立文学分析的标尺。而反过来说,也只有在整理国故这个阶段,当人们有意识面对中国文学历史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且有在研究问题中输入学理的自觉要求,新的文学观念才会与其他要素一起发挥作用,成为构建新的文学史范式的组织形式。 走向纯文学史的实践 中国纯文学史的建立,首要任务就是在上述新的文学论的指导下,根据对文学特质的认识,确定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及范围,或者说,确立文学史叙述的主体。从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具体研究状况来看,既是一个如何改变晚清阶段尚有所承袭的传统文学观念,将文学从其他学术门类中剥离、分疏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如何矫治胡适将语言文字形式分裂视为表现情感与思想工具的看法,将关注的重心由语言转到文学自身的过程。 五四新文学提倡的新的文学价值观念,在颠覆以士大夫文学样式为中心的文学传统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小说、戏曲、歌谣等的研究以及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的分体文学史走在了时代前列,而从1921年10月制订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区分已经进入教育体系,前者范围包括谚谣、小说、戏曲等,后者则包括史传之文、《文选》、唐宋八家、桐城派文等。在趋新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与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算是比较早的,皆有文学定义或界说的探讨。前者仍以康德“知、情、意”三分原则为依据(或许还有鲍姆嘉通建立与“知、情、意”对应的学科的影响),尝试将属于情的“文学”从史学、哲学等学术中区分出来,然在强调文学的“形”、“质”之分,坚持以“感情”为标准,“故言志者为文学,载道者为哲学”等认识上,显示了正确的方向;在1924年由梁溪图书馆正式刊行时,加入讲义中没有的“附录”,包括“中国文言分歧之原因”、“所谓古文”、“中国小说源流”以及“民间传说之故事”、“民间流传之歌谣”等内容,可见其用心的扩展。后者因为是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毕业的,有更新的文学观念,从在他第一编第一章“文学的定义”中的相关讨论,可见应该受到过罗家伦《什么是文学?》一文的影响,而对韩德的“文学”定义有所掌握,取材上也以文——除开小说——是主智的多,诗词是主情的多,故多选诗词;从其自述与胡适《国语文学史》的两点不同,亦可看到已有某种补阙纠偏的意识。 在二十年代初,陈中(锺)凡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的论文是中国文学走向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信号,该文依据世界文学演进的公例,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文体演进作了宏观的描述,阐释华夏民族如何由原始文学的讴谣进为古代文学的诗歌,演语言(speech)之质素而为记事诗(Epic Poetry),演音乐(Music Poetry)之质素而为抒情诗(Lyric),演动仪之质素而为剧诗(Drama);复次又由记事诗而有传记之文(History),由抒情诗而推为推理之文,由剧诗而进为演说(oratory):“诸夏文学,原于风谣,进为诗歌,更进而为散体。斯固世界文学演进之趋势,无间瀛海内外,莫能外是例也。”实际上是按照莫尔顿《文学之近代研究》中所制的表,用我国古代文学现象加以演示、论证,被认为开了运用进化史观分析中国文学体制发展之先。其后,郭绍虞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文学演化概述》与《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同样据莫氏之说立论,而于各文体演进有更为系统、详切的说明,不仅揭示出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紧扣文学之情感、想象及其形式、语言属性等特质。 这种文体演进的意识,很快成为纯文学史叙述的一种方向。稍早的如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当是其在南方大学的授课讲义,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在体例上仍是“文学史”与“文学读本”的混合,却是以文体演进为架构的,并且所录文字,“古诗”、“辞赋”多取汉魏,“律诗”、“绝句”多取盛唐,“骈文”多取六朝及初唐,“古文”多取唐宋,“填词”多取五代及宋,“小说”、“戏曲”多取元明,并述及现时之“新文”与“新诗”,“以明其现在是否有优于古”,显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化论文学史观;由其最终打消采用“浪漫”、“自然”等名词分述中国文学之派别流衍的念头来看(同上),至少于西方文学及理论亦有一定的了解。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是二十年代中期比较有名的一部文学史,当然,它的总体构架是以时代为纲的,但沈达材在三十年代的一篇书评中却指出:“此书对于各时代的文学,先用一种‘总说’来指示它的趋势,然后分门别类的按照诗,文,词,曲,小说……各个的成绩,用一种提纲挈领的方式,将各部分的代表作家,如以详细的评述……这是别的文学史所不常做得到的。”在该著第一章《太古文学》第一节“总说”中,作者在辨析中英文“文学”定义后,举述了日本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的分类——韵文:史诗-情诗-戏曲,散文:历史-哲学-演说,接着说: 最近美国摩尔登(Moulton)著《近世文学之研究》(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亦分六类。要之,此六类者,皆当以“美之艺术”为标准,其有美之艺术之价值者,文学也。不然,则今日不独历史、哲学、演说,三者咸各有独立之领域,虽诗词歌曲,然且非于美之艺术有价值,即亦不有文学之价值也。 这当然表明其接受的文学观念,在“美之艺术”的标准下,不仅文体成为文学史关注的重心,研究的范围有所落实,而且有了进一步的运用、分析原则: 今标题曰中国文学史,其研究之对象,即为中国之文学作品,不待言也。大凡所谓艺术,以形式内容两方面之调谐,为最上乘。故中国文学之研究,亦于此两者,不设轻重之别,一也。一切艺术之作品,因于时代共通之思潮,与个人独特之癖性,结合而形成焉者,故于文学之内容,又恒不能不截然区别此两者,二也。今也依据如上之根本二大原则,以为研究…… 这样,有关中国文学史研究对象及目标的论题,就由“文学”与其他学术的性质区分,开始转入文学自身内容与形式、时代思潮与作家个性等关系的层面,虽然目前尚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预设,并且这种论述及文学史分析的开展明显有摹袭日本明治时期相关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成分,但毕竟意识上有所进展。相比较之下,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初版)更值得注意。该著强调与别人所编中国文学史不同的特点,为“不以历史为文学,不叙‘载道’的古文”。具体而言,即在所谓“进化的文学史”,在第一章中,他将之分释为如下四点:一、进化的文学是活文学;二、是创造的自然的文学;三、是有文学的特征的文学,“他是含了时代精神、地方色彩、作者个性的特色的”;四、是具有形成文学的各要素的文学,“他是涵有真挚的情绪、丰富的想象、高超的思想、自然的形体的”。如果说前二点尚体现胡适的主张,后二点则已有所超越,可看到韩德、温彻斯特等文学定义的运用,以及对时代思潮与作家个性等问题的关注。因此,如其自述:“本书的分章,完全依照文学的种类;某一时代的进化的文学是什么,便拿来做叙述的主体,……可以使读者明白某一种文学由发达至衰败的历程和因果。”也就是说,该著全然采用文体演进的构架,所述从文学的起源,一直到新时代的诸体文学。 三十年代出版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北新书局1930-1933年初版)与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北平著者书店1935年初版),恐怕可以算作是这个时代中国纯文学史的代表性著作了。郑宾于在1928年4月撰于上海的《中国文学流变史》“题语”中,开宗明义: 所谓文学流变史者,盖谓这文学的源流派别是有变迁、因革的,而这变迁和因革,即是时代的创造。如“诗”之流为“赋”,演为“唐律”,再变而为“宋词”“元曲”;散文之演为各家各派的“古文”以及“杂文”“小说”之类,都是变,都是革,都是创造。 在力求系统的叙述的同时,抓住“时代的创造”的概念,展示上述文体的演进脉络,且欲在人们普遍认知的“已成”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外,察其“未著”,因而有他在是年12月“补记”所提示的第一册三章中那些“独到的”史论见解。应该说,作者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已清晰地呈现于其文学史涉略的范围中,故当时有奚行在《几本文学史的介绍》中评述《中国文学流变史》说,“作者是以‘文学的范围’为范围,而写这本‘文学史’的”,指出“在‘前论’中,作者是详细的叙明作者的立场及其对于文学本身的认识”,“又综合各家的说法而制成一个比较周遍的文学定义”,并且“作者之对于中国的作者的选择,另有两个更简单的看法,便是:——(1)胸中有了牢骚或感触,而感情又趋于激烈时,由咨嗟咏叹之间,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产物。(2)有心描写或暴露社会上的事物和情致,而用艺术的方法与手段所制作出来的一种篇什”。所谓“综合各家的说法而制成一个比较周遍的文学定义”,即其在“前论”中据标明的波斯耐特(Posnett)和韩德(Hunt)二家及未标明的温彻斯特等的主张所下的定义:“文学是基本于感情的:有思想(无论好和坏),有体裁,有想象,有趣味,有艺术的组织,有美的欣赏,有普遍性与永久性的特长,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又因中国的文学有许多不能被这原理所包括,而引申出如上实际操作的两点看法,显示其应用的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与认识,他声明: 我并不是要著古典的古文的,或贵族的文学史;也并不是要著语体的或平民的文学史。我只是要著有真正文学价值之文学底“文学史”,却不拘于古文和白话。 毋宁说,这是纯文学史的宣言。刘经庵的文学史著作标明“纯文学史”之题旨,分诗歌、词、戏曲、小说四编,各述其历史流变,如其“编者例言”所述: 本编所注重的是中国的纯文学,除诗歌、词、曲及小说外,其他概付阙如。——辞赋,除了汉朝及六朝的几篇,有文学价值者很少;至于散文——所谓古文——有传统的载道思想,多失去文学的真面目,故均略而不论。 这种文学观念,在前举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已可看到,至三十年代则成为新一代文学史家的一种标识,如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的“自序”中即曰: 至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本此文学观念为准则,则我们不但说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不是文学;即《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文章,都不能说是文学;甚至韩、柳、欧、苏、方、姚一派的所谓“载道”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文学(在本书里之所以有讲到古文的地方,乃是藉此以说明各时代文学的思潮及主张)。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 刘经庵有关“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特质”的探讨,系分别参酌罗家伦《什么是文学?》和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相关论述隐括而成,因此其界说与之前谭正璧、郑宾于的文学史无有不同,文学的范围更加明确。再从其参考的中国文学论著来看,除谭、郑两部通史著作外,尚有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大纲》、胡适《白话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陆侃如《中国诗史》以及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既可见成为经典的分体文学史在其中的作用,又显示新文学观念的文学史谱系。 这一时期,像这样的文学史如云蒸霞蔚,不胜枚举,不管是如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上海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1930年初版)、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林之棠《新著中国文学史》(北平华威书局1934年初版)、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5年初版)这样总体以时代为纲的叙述,还是如陈冠同《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初版)、贺凯《中国文学史纲要》(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初版)、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大江书铺1932年初版)、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上(文化学社1933年初版)、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北新书局1933-1934年初版)、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这样以文体演进为构架的叙述,实际上都可用如下一段评论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的“图书介绍”来概括其模式: 本书注重每一个时代的,新兴的文学,将这种文学的来源明白说出。著者的态度是把若干文体当作有机体,用发生学的方法去研究其发生和发展。旧的体裁死了,新兴的体裁替代了出来。而中国文学史遂成为一部不断的演变的活历史。 当然,与胡适执持“白话文学”的“魔障”不同,他们都是以整体性的文学范围为前提的。 作为文学史叙述主体的确立,如果说,像上面这样以文体演进为中心,体现以文学的范围为范围和普遍的进化的历史观,是一种比较明显的特征,那么,在文体背后,那些通过作家的情感、思想将文学与人生、社会表现联结起来的部分,被视作文学之内容,以及更为复杂的因果链,也是当时人们接受的新的文学观念所涵盖的文学史构成。稍早如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在其第一章“绪论”中提出:“而上文所述文学与人生有何关系,更为治文学史者,所当明瞭;然后对于文学,方有正当之观念耳。”若干年后,他在《中国文学史概要》第一章“总论”最末,仍持这样的看法,认为编辑文学史的目标,就是要“考察各时代文学体裁之变迁,及其与人民心理之关系”。上引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在阐述“进化的文学史”四个要点时所说的第三点,所谓进化的文学是有文学的特征的文学,“他是含了时代精神、地方色彩、作者个性的特色的”,其实也显示这样的体认。同样,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根据外来文学原理制定的选择中国作者的二项原则,又何尝不是从文学与人生、社会的密切联系着眼。还有像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第一章“导论”对“文学史”的解释:“作者要有历史的精神,具备一种批评的眼光,做到说明(to interpret),证明(to verify),鉴定(to judge)的程度。还不要忘掉文学为生活的表现,不惟对于文学作者个人生活有精细的探讨,对于产生文学的时代精神,社会环境,亦须有真切的认识。”也提醒人们这是文学史的任务。 因此,在二三十年代勃兴的那些文学史著作的具体叙述中,本着那种“历史的精神”,文学史家日益关注时代思潮与凸现这种时代性的作家个性,大多会采用像陈冠同《中国文学史大纲》“导言”中所叙的构撰方式:“每一时代,每一流派,每一作家,凡可以代表一时代的精神,一流派的作家,或一作家的作品的事实,都详加叙述;其余则用鸟瞰法,提纲挈领一叙。”文学流派、文学群体以及某一文体下的集体创作活动相对受到重视,并由此揭示时代文学之特点。如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论述各时代诸体文学,不乏诸如“汉代文学的倾向”、“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潮”、“唐代的文学运动”、“宋代的文学运动”、“明代的文学运动”之类的设置;而在讲“魏晋南北朝文学”时,先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潮”一章概述其总的文学特色及来源,如何受当代思潮——老庄和佛教的影响,离开了实际的社会与人生,受当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主张唯美主义的文学;然后以贵族与文人阶级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两章分述各时期诗歌,无论是前一章从“竹林七贤”中寻出阮籍,在太康文学“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中标举左思,在东晋至宋诗中树立“于向来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以外,屹然别立一宗”的伟大诗人陶渊明,以及“能继陶潜光辉”的鲍照,还是后一章表彰“表现作者热烈的生命”的南方民歌,“北方儿女英雄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木兰辞》,都显示了其所具备的一种批评的眼光,以坚持写出沉挚的深情、朴素而自然的风格为文学的价值所在。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论述“唐代的诗歌”,在着重分析“近体诗之完成”、“近体诗与音乐”作为其时诗歌兴盛的内在原因外,一改人们依据高棅划分四期的叙述模式,而采用“绮靡派及其反动”、“边塞派与自然派”、“社会派怪诞派与脂粉派”的流派叙论法,其实也是以风格把握文学内容与形式之统一性的初步尝试,让读者看到诗人们的创作对于生活与情感的各种富有代表性的表现。 这种文学史构成,或亦可视作是胡适明变、求因、评判的史学方法与新的文学观念融贯而后的进展,然从文学史理论的影响来源来说,泰纳(Taine)“时代、环境、种族”三要素的学说,无论在东西方,毕竟有其不容忽视的范式作用与地位。韦勒克认为泰纳文学批评的标新立异处,即在承黑格尔的历史观和艺术观,提出文学作品的“代表性”问题,相信伟大的作品乃是时代的结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因而也是历史性和民族性的“代表性”和“表现力”,从定义上讲,既是艺术价值的结果,也是原因。而其理论的矛盾、复杂的张力,除了为像勃兰兑斯(Brandes)这样的文学史家开启了文学社会学的面向(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即以更突出“时代”因素而对中国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在像韩德这样的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学者身上亦有所体现。如果韦勒克对于泰纳的评判——“身为批评家,他提示出文学社会学中的种种问题,但它更为成功的是点明个性特征而且分析了作家及其类型和理想的世界”是准确的话,那么,韩德在参考泰纳的三要素学说说明构成文学生活和变化的条件时,加上“人格”或“个性”之第四个要素,正显示了是基于泰纳理路的发展,如他在该著的另一处指出的:“心的行为,精神的运动,和文学的表现,在一切民族都基于同样的基本原则上,而作家或各别文学之最能讨论,解释和流露这些冲动和思想的,就最能接近普遍的型。” 中国文学史上述内在构成的形成,显然受到以泰纳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社会历史学派的陶铸,故如余冠英在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所写书评回顾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之“显著的进步”时,总结的第四条即为: 由于西洋同类著作的影响,写作方法渐渐改变,由经史子集的概论或文人传记与诗文评的集合体变为叙述文学主潮,阐明因果法则,有合理系统的中国文学史了。从师承授受的记载走向用几个基本因素来说明文学的进展了。除文学本身的观察外知道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来研究其与文学现象的关系了。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较而言,这些文学史著作在揭示作家个性及艺术特点的作家论方面尚未完全成熟,那种“对于文学作者个人生活有精细的探讨”其实并不多见,更不用说精细分析如何用艺术的方法与手段来制作,而往往较多采取传统批评现成的资源,甚至还来不及完全转换成现代的叙述语言。在这一点上,如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固然显得简陋,如第一编第三章“魏晋的诗歌”中有关曹植的叙论,虽誉为是“可称屈原以来的第一个大诗人”,全部不过是如下数行常识: 曹植(192至232)字子建,操之少子,因他被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世人又称之为陈思王。他幼有才思,十岁即善属辞,有“七步成章”的佳话。不幸为其兄丕所妒,郁郁不得志,因之发而为诗,不惟情绪直挚迫切,铸词亦极精妙绝伦,无怪乎他的作品,驾于他的父兄之上,为当时诸文士的领袖了。谢灵运曾说:“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钟嵘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因之在他的《诗品》里,把曹植列为上品,这可见子建的才调,和文章是如何的富赡精美了。有人说,他的诗哀而不伤,有如贵宾,我们看他的《七哀诗》《瑟调歌辞》和《名都》等篇,即可知之。 提出这项任务的张长弓自己,亦大半做得比较粗略,如其论李白,亦只是蜻蜓点水式一叙: 李白是唐之宗室,因为居性傲放,不容于朝。遂作一个山林隐士,自适于天地间,足迹遍名山,因之山水的咏作极多。他的天才高、见解也高,真能欣赏自然的美;而文笔又复恣肆豪放,不受任何的拘束,所以他的成就很大。如他的《山中问答》,《独坐敬亭山》,《自遣》等作,皆为极佳美的自然咏歌。 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文体演进或流派风格叙述构架的制约,但从文学史书写现代转型的整个进程来看,是否亦意味着在注重方法与系统整理的目标下,中国文学史知识体系实现由传统型态向现代学术的转换,本身需经历一个由构架到深层肌理的渐进的更新过程。作家论作为一种更为内在的组织构成,其更新相对迟缓,真正达到成熟,恐怕要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撰作那样,在比较充分地借鉴西方文学研究中作家论的研究方法与要素之基础上,综合运用新的传记学、社会学、心理学及风格论等多种手段才行。 余论 综上所述,二三十年代中国纯文学史的建构,是中国文学史知识体系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它的兴起与壮大,毫无疑问,有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进化论史观以及新的文学价值观念所构成的现代学术立场的基础,有“整理国故”运动导向进一步学术本土化的观念及机制上的促进,有“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的自觉要求与系统性的西方文学论的引入,是确立“纯文学”为主流文学观念的产物。不过,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纯文学”观念的发展路径相比较,中国现代社会的这种“纯文学”观念有其自身的特点,尽管以想象、情感、思想、形式四要素作为文学的特质已深入人心,据此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态、价值得以确立,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亦因而确定了自己的叙述主体,然其与那种视文学为纯粹审美经验的面向尚有不同,真正的形式史或作为文学内部研究的文本批评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并未出现。与此相关,20世纪作为精神科学的文艺学主张的“个别化的方法”,与实证主义那种在精神领域移植自然科学的“一般化的方法”的对立,亦未在现代中国真正形成,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日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很快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接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纯文学史的建构尚是一条未走完的路。 在另一方面,即使是面对这样的中国纯文学史的建构,在那个时代其实也有不同的声音。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这样在新文学已成为文学正宗的情势下,仍以“从《史》《汉》笔法中揣摩出来的文学史方法论”构撰其近代文学史,被认为“只为旧日各正史中所有《文苑传》之扩大耳”,或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还有同样运用新的西洋文艺理论与新文学人士进行论争者,那恐怕主要来自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学者阵营。郑振铎指目“学衡”之“古典派”,说“他们当时都是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教书,彷佛是要和北京大学形成对抗的局势”,但在1925年吴宓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后,亦应与有英美留学背景的清华学人相联系。其分歧大抵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对于“主情”的纯文学观念的质疑。这种质疑的理论依据当然在新人文主义所提倡的文学应表现人文道德与理性,反对新文学对于情感想象单向度的无限张扬,然对中国文学史的建设来说,也是对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断裂”的有意矫治。故如吴宓针对新文学论者“谓凡文学以情感为主,说理叙事均非文学”的议论不以为然,认为“盖皆由不知文学之范围实与人生之全体同大”。钱锺书同样从对以“知”与“情”的绝然分划作为“纯文学”与“杂文学”内质区别的质疑开始,却进一步指出其症结在于“夙囿于题材或内容之说”:“究其所失,均由于谈艺之时,以题材与体裁或形式分为二元,不相照顾。” 他举六朝萧统《文选序》与刘勰《文心雕龙》之别为例,认为前者“一以题材为准,均采抒情言志之作,不收说理纪实之篇,……其所谓‘文’,为义极狭”,“近论多与萧统相合,鄙见独为刘勰张目”,说到底,“论文者亦以‘义归翰藻’为观点而已矣,于题材之‘载道’与‘抒情’奚择焉”。正是鉴于主“情”的文学观念淆乱各种文学样式间的界限,他们主张文学诸类型各有其体性,如吴宓在《诗学总论》中详解诗与文的内质与外形之别,钱锺书则从传统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出发,坚持“文各有体,不能相杂,分之双美,合之两伤”,用意皆在会通中西古典文化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更富有张力的文学边界。二是对于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的质疑。其理论依据亦来自新人文主义对于科学实证主义的挑战,不赞同文学史与生物进化之间的类比。如梁实秋就认为,“在文学艺术里面,无所谓退步,亦无所谓进步”,“古代作品绝不逊于近代”,那是因为“文学作品以基本的普遍的人性为对象者,其感动人的力量,便是永久普遍的”,从所谓共时性的视角,强调文学的恒久价值。吴宓亦认为,“文学所表现者,乃人生及人性之常,兼及其变”,而对“只注重人生人性之变,而遗弃其常”的浪漫派文学等提出批评,同样从以永久性作为文学的本体特征立论。钱锺书后来在梳理近世文学史上类似“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时,更就文体本身着眼,反对机械的文体演进论,认为“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这可以说是在文学史观上与新文学主张的较量。三是对以西方间架构筑中国文学史体系的质疑。中国文学史体系实现现代转型,明显是以现代的文学观念、进化论文学史观为要素,先完成外在架构上的新变,这一架构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的实态,是否能在较深的肌理层面真正建立起文学和历史之间的某种联系,本应得到及时的反省。刚从英国留学归国,已在清华大学执教的朱自清,曾自记与浦江清的谈话(浦江清曾在与白璧德、穆尔共倡新人文主义的薛尔曼辞世后,译出其《现代文学论序》,刊于《学衡》第57期),谓:“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所谓“抹杀”,就好比我们今日反省时所说的“控制”与“遮蔽”,显然已认识到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实施这样一种古今对立的学术现代化方式不可取。钱锺书的说法更为激烈:“作史者断不可执西方文学之门类,卤莽灭裂,强为比附。……文学随国风民俗而殊,须各还其本来面目,削足适履,以求统定于一尊,斯无谓矣。”这固然体现他们在文化实践中注重传统延续,将所接受的新知置于自身的历史语境予以观照,建立合理的古典研究的诉求,背后则还是一个在中西文化大背景下如何通过自我文化认同选择现代出路的问题。 中国纯文学史的建构,正是在与上述种种不同立场与话语系统角逐的张力中进行的,这种复杂的格局,除了决定其呈现的面貌及发展走向,还让我们比较真切地领略到那个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多种探索与认知,它所经历的历程,无疑为我们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重建古今联系,寻求中国文学史建设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经验。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陈广宏教授 原刊复旦大学古籍所编《实证与演变:中国文学史研究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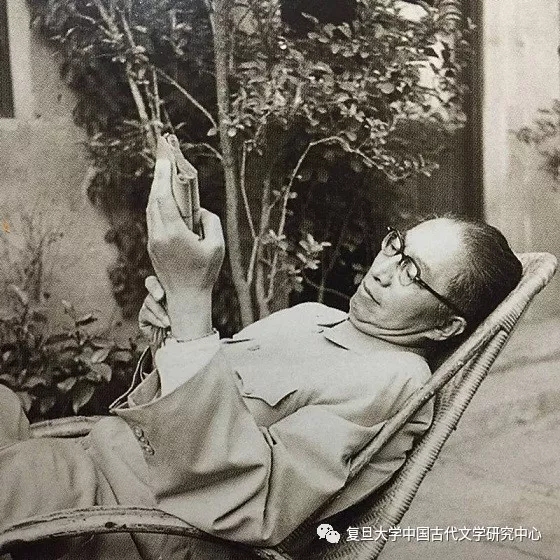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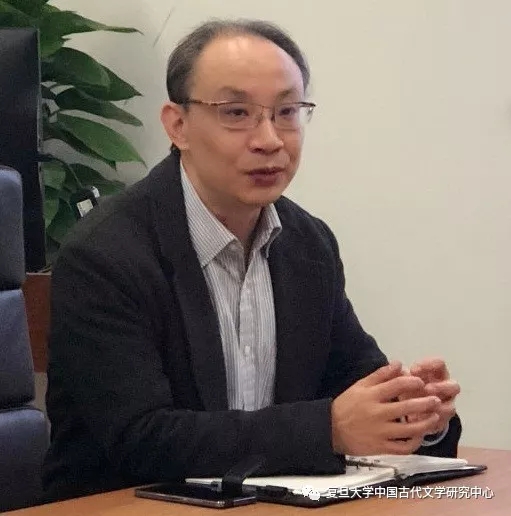
|
|
|
|
|
|
|
|
|
|
Copyright © 2013 |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电话:021-65643670 邮编:200433
| 历史访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