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自由神俗通 ——杜德桥《神秘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广异记〉研究》译序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四十余年里,《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出版了二十多部汉学专著,既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又有着大致统一的学术风格,展示了新型东方学学术魅力,在欧美汉学界一直有较高的认可度,多数已成当代汉学经典,被列入各专业的必读书目中,如:康达维《汉代史诗:扬雄的赋的研究》(David R. Knechtges: The Han Rhapsody:A Study of Yang Hsiung),戴维斯《陶渊明的作品及其意蕴》(A.R. Davis: Tao Yuan-ming: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葛蓝《庾信的〈哀江南赋〉》(William T. Graham: The Lament for the South: Yu Hsin's Ai Chiang-nan fu),梅维恒《敦煌的通俗文学》(Victor H. Mair: 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艾朗诺《欧阳修的文学作品》(Ronald C. Egan: The Literary Worksof Ou-yang Hsiu),伊佩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斯坦利《唐代的佛教》(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韩明士《政治家和绅士:两宋时代江西抚州精英》(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贝蒂《地区与宗派:明清安徽桐城县研究》(Hilary J. Beattie: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等,都成为各领域中标志性成果,这些作者多因此而登上国际汉学殿堂。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第一部论著《十六世纪的中国小说〈西游记〉的故事原型研究》(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是他博士论文,也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时在1970年。他以此为起点,佳作连连,登上了中国古典小说与古典文献学学术高峰,先后担任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欧洲汉学会主席。在二十五年后,他又为这套丛书贡献了《宗教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戴孚〈广异记〉》解读》(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展示了他在这个领域里取得的新成果,也推升了这套丛书的学术高度。这套丛书多部已被译介到中国,杜德桥著作却少有译本,唯台湾巨流出版公司于1990年出版了他的《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中文译本,杜氏在序中言:“西方汉学家看到自己的著作被中国读者细读与补充,实是他所能期望的最好反应了。”已表达了欲与中文读者交流的愿望。他曾自谦地说:自己的想法太怪,翻译不易。言语之中流露出不少遗憾。本书的译介与出版可稍许弥补这一缺憾。本书是杜德桥教授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学识水平、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对于国内读者了解他及西方汉学话语体系甚有益处。从笔者角度看,以下几点尤值得关注: Glen Dudbridge: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一,新颖深邃的学术命题与自成体系的研究思路 本书以七篇论文与《广异记》译注二部分构成,但不是松散的论文集,而有着严密的学术逻辑与结构。作者一再申明他的学术思路,强调全书结构的系统性。他以解读《广异记》为基础,具体研究唐人宗教世界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分析其中的宗教意识与世俗观念的联系。实际上,就是研究唐人世俗化的宗教意识。他所说的“宗教”,既不是单一的本土道教,也不全是外来的佛教,而是流行于现实社会之中以道教为基础集合了多种神灵意识世俗化的宗教行为、宗教观念与宗教意识,它不是对一种神的崇拜,也不执着于一种统一理念的信仰,更多是一种宗教化的传统意识与一种神秘化的神鬼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作用下形成的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与相关的祭祀活动,多数属于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各种各样的“以鬼为邻”的“迷信意识”与“迷信活动”。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宗教体验”。书名所说的“世俗社会”,就是世俗化社会阶层,他们不是上层掌握正统话语权的皇亲国戚,高官权贵,也不是纯粹的佛家僧侣道家道士,更不是严格意义的教徒,他们多为普通的中下层属吏或下层市民,这是《广异记》中的主要人群。对于作者来说,《广异记》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由这些人构成的世俗世界。他发现在这个世俗世界里,所有宗教理念与宗教行为都有世俗化的特色,所有宗教行为都是在世俗生活中产生并进行,参加者多是世俗中人,而且,所有宗教行为都有世俗化的原由。所以,本书要研究的核心就是唐人宗教信仰世俗化的问题。全书的结构就是围绕这一核心话题展开的,如: 第一章《一个声音的序列》说明本书主旨,通过分析三则鬼附体故事,指出这类叙事中存在着二种故事形态,一是由故事主人幻觉构成的内部故事,另一是由记录者或旁观者所见事件构成的外部故事。故事中包含着传统理念、故事主人与记录者三种声音。具体探索这二个世界的内容以及多种声音的构成,就是本书研究内容。如其言:“《广异记》以及与它类似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遥远时代的口述历史。当时的普通人对他们的时代、生存环境以及切身体验的陈述都掩埋在这几百则轶闻中。我们研究它们,不是想通过文献性材料去构建关于那些事件与制度的知识,更多的是想探索逝去已久的那代人在面对周遭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时产生的心理体验。”“将世俗旁观者的视角与身在局中者的内在视角区别开来,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则:在同一件叙事中,辩识出并存的两种视角。”并提出了研究原则与方法:“要求研究者对当前时代有一个鸟瞰的高度和宽广的视角,以现代思想观点,将各种历史文献置于一个看似有意义的序列中。另一个是我们研究工作中更基本的本能,那就是想了解并接近过去的男人与女人,以私人纪录来不断激发我们转瞬即逝的兴致,……它最强大的作用是运用少有的机会去捕捉当时的人们在生活中的特定时刻如何活动,如何表达自我。” “力图识别材料中隐藏的具体个人化情境,从而在与他人纠合在一起的声音中区别出个人声音的核心内容。”说明故事人物“所处的文化环境如何装点了他的思想。”宗教世俗化,这既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人类发展经常遇到的问题。作者思考的反映是一宏大主题,但入手是具体而微的,是对具体故事进行现代化的解释,发掘表象后的内幕。第二章《同时代的一种观点》,通过笺解顾况《广异记序》,具体介绍《广异记》一书以及作者戴孚的基本情况。以此说明《广异记》所叙鬼神观念不是孤立的,它有一个古老传统,广存于当代人精神世界里。第三章《戴孚世界的动态变化》,相对于第一章从时间上说明故事特点,本章着重从空间角度说明《广异记》世俗世界,进而更具体阐述本书的研究理念、基本对象与基本方法。作者分析了唐人普遍存在的与鬼邻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关于阴间的空间意识,强调与“人鬼殊域”的正统观念相比,这是一种更加世俗化,却又普遍化的社会意识,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分隔。运用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划分法,以《广异记》中“桃花源类故事”为例,说明这些故事中存在着自古不变的因素、看得变化的因素以及当下事件三层因素,对于后者,作者即关注到安史之乱引起的政治格局之变化与禅宗兴起引起的新兴民俗。以下四章是对上述概念的具体实践。第四章《华岳的崇拜者》,说明与朝廷正式祭祀华山不同,民间还存在着以华山为对象的淫祀活动,形式多种,多带有世俗功利性质。这种能满足人们各种目的华山神有一定的地域性,并作为一种地方神发挥影响,其影响力可以扩散到很远的地方,作者以此说明非官方地方性的世俗化宗教意识在唐代影响更大,其中存在着长久的察觉不到变化的远古信仰。第五章《尉迟迥在安阳》详考安阳祭祀尉迟迥之事的背景,辨析正史记载,石刻文献,轶事传说同异,分析其中原因与影响,由此总结出民间宗教的世俗化特点,说明城隍文化意识产生之源。第六章《袁晁之乱的受害者》,通过解析几则亡灵与活人交往的故事,说明这类传说中包含的久有的鬼魂意识,唐人的葬礼中道教、佛教因素,再以魂灵预测战乱之事,说明安史之乱在人们宗教意识中投下的历史痕迹。“我们通过这一途径所接收的信息引领我们接近正统文本文化之外的宗教体验与人物。《广异记》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中的那些女人或奴仆。在那些人中,没有人有条件或能力以文字形式表达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私人看法。在公共历史事件的接收末梢,同时也是在动态的历史情形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世俗社会人与人之间、活人与死人之间典型的交往与联系。这些人物的话语来自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社会关系、宗教价值、神话概念皆不受制于被广泛认可的正统观念。”第七章《与鬼神交欢》,分析几则与神女、鬼女交往的两类故事不同的心理机制:一是世俗婚姻的理想化;一是与冥婚习俗有关的想象,说明二者既延续着类似《神女赋》、《高唐赋》性爱意识与古老的冥婚制传统,也有安史之乱后新的社会因素在其中,更有叙述者自己的声音与当下意识[1]。 由上可见,本书重点就是研究《广异记》中与附体、通灵相关的人鬼交往故事,前三章是相关理论概念、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的说明,作者指出这些故事所表现出的神鬼观念,对于当时人来说就是一种信仰,它们表现了唐人对这种信仰的具体体验,所叙之事就是唐人思想的历史记录,这里面有远古传统,有中古佛、道意识,还有当代思想因素,在陈述者世俗 化想象与病态意念中组合到一起了。作者将医学生理分析与文化解析相结合,分别说明这三方面的内容。后四章就是在这观念基础上展开的四组个案研究。华山神事说明朝廷正宗观念与世俗观念及地方化观念之差别;尉迟迥故事,说明地方性的传说如何改变了正史正统之说;浙东逃难故事表明中古传奇模式中有当下的时代因素;人神恋、人鬼婚故事可证明遗精梦幻体现了不同的时代色彩与当下意识。七篇文章有点有面,构成一个整体。作者在之前已写几篇关于《广异记》的论文[2],本书收入后,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体系的完整性。 杜德桥(Glen Dudbrige)像 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复合式视角 在现代学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上,《广异记》是一部唐人志怪小说,属于作者有意设幻的文学作品,杜德桥在掌握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更多的吸收了现代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研究思路,以《广异记》为八世纪精神史记录,解析各类通灵故事中文化要素。如他所说:“在欧洲,它(《广异记》)已引起了人类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的注意,他写道:‘它们构成了研究中国民俗极富价值的文献资源。’”“虽然作品创作的年代相差很大,但整个阶层在特征上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在万物有灵论上,即使是最细微的变化与进步我们也难以追溯,这可以旁证我们的判断:中国社会在整体上一直就是这样的。”杜氏又利用布罗代尔年鉴学研究观念以及福柯知识考古学理论,展开了新的探索。如他所说:“为了研究故事中人物个体的声音并区别内部故事与外部故事,本书尝试一种更具分析性的研究思路。同时,它也通过辨识特定时代与空间中的个体,来研究其历史特性。但它又与高延的基本观点相合,即把《广异记》作为一本实实在在的记实文献,而不作为奇幻故事或虚构文学。”同时,他对于《广异记》作为志怪小说的性质已有了充分的了解,他说:“进入二十世纪,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研究者开始对文献的价值与种类进行重新界定,虚构性的叙事已上升到了经典性的地位,古代 “小说”这个词被用来支撑这一概念。在当下新的思潮运动中,中古时期的轶事文学作为原小说——这是一个可以觉察到的小说演进过程的早期阶段——引起了史学家的兴趣。而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唐代则是小说创作的黎明时代——这一观念早在十六世纪就有人表述了,它已成功地覆盖了更多的古代观念。”作者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有意识要以这种跨学科的探索改变既有研究格局。在突破了“文学虚构”这一既定思维定势后,新的视角给作者带来了新的思路,在许多被文学研究视为模式化、雷同化的叙述中,发现了新的学术命题,为这些文献注入新的学术生命力。如:众多还魂类故事,多是千篇一律叙述“阴曹行”,但是作者却从中看出了故事中几种不同层次内容:主人迷幻意识(生理的)、阴间知识(集体无意识)、职业通灵人特定的唤魂或驱鬼活动(当下心理),发现在《广异记》的世界里,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乃至阴间与阳世都不是截然分开的。他说:“《广异记》提供了一系列来自于街头巷尾的感知过程。”“越是深入到《广异记》的内部,我们越会发现它潜藏的一种特质,可以称它为“民间性”(vernacular)特征,”“社会精英不仅仅参与由朝廷科举体系形成并由国家官僚机制执行的高级文化,而且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到他们周围丰富的地方文化环境中。《广异记》故事就是在后一种背景中形成的,它记录了当时的男男女女在其生存背景下遇到非正常现象时的感知过程。戴孚并没有让这些现象的记叙屈从于中央权威做出的评论或拒斥,也不屈从于批判性的正统思想的重新阐释。因此,《广异记》的故事比那些精英们写出的精心构思的正统书籍更能代表广大民众,它们揭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的诸多特征,同时,这种背景下也存在着精英创作与士人活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民间文化是海纳整个社会群体的。”杜氏发现戴孚在《广异记》中构成的世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具有民间化世俗化色彩,在这个世界里,宗教与世俗并行不悖,这里的成员多是世俗社会中下层成员,但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多以世俗化理念来体验他们的信仰,正是这种俗气意识才使得这类宗教类故事富有生机。 如,杜德桥认为《广异记》故事里既分隔又对应的阴阳两界观念,既源自于戴孚社会的深远的精神世界,也反映了这个精神世界的不同的历史变化,因此,其对阴间世界的描述也可作为唐代社会史料。杜氏认为“将中国社会分成南部与北部,或者用特定身份类目来界定,如京城与地方、都市与乡下、贵族与平民、受限制的与自由的。在每一个故事中,戴孚都是以一种宏大的、乃至多元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最强烈的特征就是它的灵活性与不稳定性。”“《广异记》表现了由很多小地方组成的中国社会,这些地方构成了一个松散的动态的系统,其特征是自由的多样性的组合,而不是两种对立的类别。”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极度的世俗化化解了这些界线。在《广异记》里的阴间世界,是与现世完全对应的世俗化世界,两者区别仅是意念中阴阳界线与空间区域。“《广异记》最引人入胜的奇遇多数发生在远行者或者离家者身上。那些被阴间的王召去的人都会程式化地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城墙之外——经常通过一道关闭的门——穿过广阔的原野后到达另一世界一座森严的城堡。不论情况如何,大部分农民和土地主都依靠田庄生活,他们的住所在城外,与乡村的关系密切;田宅庄园经常是与神灵世界保持频繁接触的场所。”“《广异记》故事显示这种分离是脆弱的和有缺陷的,它们之间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因而,凡人和神灵,活人与死人能够持续而不定期地越过他们自身的边线。而摆在唐代祭司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这种越界行为的发生。”这既是一种民俗心理分析,又是对一种文学场景设计的发现。新的视角带动出了新的发现。 李公麟(传)龙眠山庄图一 绢本 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杜德桥多受法国年鉴学派及结构主义文化理论影响,善用多维立体化的学术思维考察各类故事,认为“没有一个故事具有超越与周围世界所有关系的独特性,但也没有一个故事能对中国社会做出一番完整、无限与永恒的陈述。这需要一种历史性的阐释手段,创造一个故事存在的语境。同时,还需要一种时代意识,一种能赋予那些异闻记录以具体意义的时代意识。”他将这些故事视为文化化石,既要将它们置于特定时空中,分析其具体的历史痕迹,又要挖掘其时代表象之后亘古绵延的文化传统与信仰观念。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既要测定各类故事中不变的文化基因,又要分析年轮印记与外在构成。如他所说:我们将把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文化,看作一个以不同速度同时演进着的综合体。把它比喻成水流运动最恰当不过了,它运动的形态是:深处缓慢流动,表面急速流淌,充斥着无规律的潮流与区域性的水涡。然而,这个比喻虽然很有启发性,却很难有效地使用。因此,我采用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案,这是借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历史变化有三个层面的著名观点:首先“一种历史的过程几乎是难以察觉的……它的所有变化都是缓慢的。”其次,“另一种历史……它有缓慢的但能够察觉到的运动节奏。”最后一种是“事件的历史……有简单的、快速的、紧张的起伏。”如《仆仆道人》是流传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故事,其影响甚大,光州乐安县还缘此改名为仙居。(最近,日本玄幻小说作者仁木英之将之改编为系列小说,影响甚大。)杜氏关注到故事中这一细节,“仆仆道人自言:那些经典人物都曾师从于他:‘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三茅之属,问道于余,余说之未毕,故止,非他也。’”他一方面由狂热病理与幻觉心理学层面分析噫语通神者的情节成因,又一方面又认为此处显示了以上三种要素的不同形态:一是表明当时道教上清教以及以茅氏兄弟命名的茅山已在中国社会主流意识中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二是展示了七世纪上清教的师承关系:陶弘景(456-536)传潘师正(585-682年),潘在嵩山退隐后,传司马承桢(647-735年);三是上清教在嵩山的影响。三个层次的事情涉及到三个时段因素,“比官方传承的正统经典记载更能有力地揭示世俗社会对道家先圣的看法。”这则为这类故事找出了年轮印记,这是年鉴学派的研究风格,于动态把握中扩展了关于这类故事的研究空间。这一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使他能突破了文学研究框架,可充分发掘这类故事的思想史、文化史信息。这里既有明确的文献、史实的考辨,如关于陶弘景——潘师正——司马承桢的师承关系以及嵩山道教的中心地位;也有现象背后的分析归纳,杜氏由此还推导出天宝道教最高层次的思想已普及到民间低层这一事实,突出了天宝道风迷漫的时代特色。前实后虚,不同层次,组合成关于天宝年代文化流向的立体图景。杜甫曾回忆这段历史言:“蓬莱宫阙对南山,云外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借助这种立体化的图景,可对此有更真切的认识。 总之,“世俗化宗教体验”的理念,多学科多层次的叠合式的研究方法,应是本书以及作者学术最具特色的地方,对于中国学人来说,这也是“他山之石”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三,文献考据、文本笺释硬功夫与东方学学术魅力 在西方汉学界,关于《广异记》研究,杜德桥并不是第一人,早在上个世纪初,高延在他的代表作《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已有关注,译有三十五篇,并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受其影响,西方多个研究中国古代葬礼、祭祀文化的学者也多利用《广异记》一书,杜氏在他们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系统研究《广异记》。与前此相关论著相比,杜书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文献考据上的细密严谨的风格以及实实在在的发现,展示了一个汉学家不凡的专业功底与实力。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语词训诂,既见汉语功底又有新意新解,如,顾况《戴孚《广异记》序》第一句曰:“予欲观天人之际,察变化之兆,吉凶之源,圣有不知,神有不测。”他解释到:“开头的话出自《尚书·益稷》:‘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 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他取古文《尚书》作为笺释材料,与传统的取用《易·系辞》不同,显然,他没有今古文概念的制约,唯以文字相似度为上。同时,也为了下文对观的解释提供证据。他说:这里的“观”是古代朝廷一种天赐的职责,由下文的“天人之际”所决定。而“天人之际”表达的是一种传统的现象主义宇宙观,是由汉代承袭下来的意识形态。“际”意思是“相联系的界点”,指的是人与自然界处在一个相互感应的系统里。此处解释是在传统训诂基础再作引申,这种引申又是以其前辈汉学家李约瑟经典之论为据。李约瑟《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卷2(剑桥 1956年,378页。)言:“伦理的失序应该与宇宙图式某一处的失常息息相关,而这种失常必会引发人世间其他方面的混乱。这种混乱不是直观的行为表现,而是一种震荡,这种震荡是通过有机整体的巨大衍生物所显示出来的。”他据此解释古代的祥瑞凶兆之说,指出“因为这种失序给古代君王提供了宇宙伦理秩序是否正常的指示表,只要是英明的皇帝,他们都希望能够控制这些非同小可的混乱。”又引《庄子·天下篇》:“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为之圣人。“解释了“天下之兆”。此处以道家思想来笺解,可能更符合原文之意,因为顾况本人是道教徒,《广异记》也多道家色彩。又如:他同意顾况改经释义的做法,训“子不语怪力神乱”之“来”为“示”,并在儒典中找到旁证:“《周易》附录的《系辞》中也有与许慎这种说法类同的语句:“天垂象,以示凶吉,圣人以象作之。”并说明:“对于统治者来说,观象施政的理论是完全正统的;而对于世俗之人来说,把一些怪异现象作为避灾趋吉的征兆来看待,也不是奇怪的事。”显然,他对传统经学笺词释义知识系统很熟悉,但又不固守既定模式,尽可能发掘出新意。 其次,在文献目录学方面有积累,如他发现《全唐文》所收顾况序文本比《文苑英华》粗糙,其因就是《文苑英华》本经过了彭叔夏校正。他广引书录,对顾序作了原创性笺释,这些书目分二类:一为相关用典的出处,如贾谊《鵩鸟赋》、《左传》(齐王遇梼杌)、《庄子》、《吕氏春秋》(苌弘)、王嘉《拾遗记》、纪义《宣城记》以及《淮南子》、《山海经》、《后汉书·五行志》、干宝《搜神记》、郭璞《抱朴子》、扬雄《蜀王本纪》、左思《三都赋》、《鲍照集》、萧统《文选》等。二是自汉以来的志怪专著,如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东方朔《神异经》、张华《博物志》、郭宪《武帝洞冥记》、颜之推《稽圣赋》、侯君素《族异记》、陶弘景《真诰》、周子良《周氏冥通记》、刘敬叔《异苑》、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冥录》、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杨方《楚国先贤传志》、应邵《风俗通义》、宗懔《岁时记》、山谦之《吴兴记》、周处《阳羡风土记》、沈怀远《南越志》、葛洪《西京杂记》、伏无忌《古今注》、崔豹《古今注》、萧世怪《淮海乱离志》、裴松之《三国志》注、陆澄、刘昭《两汉书》注、刘彤《晋纪》注、刘孝标《世说》注、盛弘之《荆州记》、张说《梁四公传》(或曰卢诜、梁载言)、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张荐《灵怪集》等[3],尤其是对已佚之书在吸纳内山知也、李剑国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新推断,并以异域传奇、魔幻物件、预言报应、幽灵活动对各书做出不同的归类,突出了它们的特色,展示这些书籍与《广异集》的关系,凡此都显示出了杜氏在文献上深厚的积累。对顾序,他还注意到书籍史上一段重要文献:“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他据这些信息推断:“每页十行字,每行大约十个字,一页计一百字,那么一千页大约共十万字。”这个推论是很准确的,这表明顾况当时所见的《广异记》可能是册页装,每页十行行十字,呈正方形,与盒式贝叶装长条页是不同的。据此书籍史上关于册页装出现的时间可适当提前。杜氏据此还指出“我们集合保存在《太平广记》中的三百余则故事以及在《类说》、《岁时广记》、《三洞群仙录》、《太平御览》中所录的其他六则材料,估算出本书现存约八万字……我们现在所见的《广异记》仍然保存了八世纪末戴孚儿子向顾况求序时的那本原书的大部分内容。”正是有了这种文献史意识才会于细琐处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发现。 三是在史实考辨上多有发现,如关于戴孚生平,此前少有专论,杜氏在排比材料基础上,对之前内山知也说法提出修正意见。他叙述了戴氏家族史,由戴逵、戴颙多浪漫之举看出:“所有这些都证实,至少在逸事趣闻这一点上,戴氏家族戴孚一支与苏州有较深的渊源。”再由戴孚于至德二载(757)与顾况(725-806)同年参加苏州进士科试一事推断戴孚生平,“我们根据《广异记》故事得到戴孚一个更详细的活动年表。这些故事在时间上大体贯穿八世纪,直到780年叙事才突然中止。戴孚卒年一定不早于这一年,也应该不会比这个时间晚得太多。假如他的卒年为五十七岁,由此推出他的生年最早是724年,顺此推算,他及第的年龄可能是三十四岁,这个年龄与顾况相差无几,顾况约是三十岁,当然戴孚年龄可能更小些,但不会小于二十岁。如此算来,他的生年不应晚于738年,卒年不会晚于794年。在第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有很多故事反映了在八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在东部沿海地区官僚圈中的社交活动,也许这是了解他仕履最可靠的线索。”其推论逻辑严密,结论大致可信。又如本书最后一章《神女的故事》所引第一则材料就是季广琛与神女交往的故事。季广琛是李璘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但正史并无他的传记,本书进行了原创性考证:“季广琛于735年应“智谋将帅科”中举,757年初,作为永王李璘的一名将军,他被遣远征至长江下游,这后来发展成一场未遂的叛乱。然而,在当年三月永王叛乱被镇压前,他成功地脱离了永王。在758年夏秋,他很快由一个地方的军事总督移任至另一地。759年,被贬为温州刺史。后来,在761年,他由温州移任到宣州,担任浙江西道的军事职务,在这之后,他最终在774年升任右散骑常侍。”并据此印证故事的结局,“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又引《酉阳杂俎》卷六中一则季广琛故事,“青春乃知剑之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翰镇西凉,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之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杜德桥指出:“748-755年哥舒翰率领军队在相邻的陇右地区抗击吐蕃……故事中的季广琛在河西的这段奇遇似乎发生在他参与永王谋反之前。”经过如此勾稽,季广琛生平信息首次完整起来[4]。这种搜辑文献的方法与考据路数,都是中国学者熟悉的。这一点也是杜氏在欧美汉学界最具特色之处。 关于英国汉学,中国学人多较熟悉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于《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 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 ……并在公元 3 世纪到 13 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科学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本书第一章言: “为什么现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乌、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长期思考,早在1942年李约瑟第一次到中国时,即以此问质疑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王氏受此刺激,写下《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在传统知识结构中,西方学人视汉学为东方学分支,以辨析语义与辑录稀见材料为主要特色,汉学家多以汉学为异质对像,最大的兴趣就是求索其中异质特征,虽然各自关注的异质点不同,但核心命题多与这一终极关怀相关。杜德桥的汉学思维也就承此传统而来,其思考的核心话题——中国宗教世俗化问题也属这一类。在他看来,对宗教的态度不同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世俗化的宗教意识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他的学术兴趣就是解析这一特点的具体特征、内部结构系统与形成机制等问题。他最初从事《西游记》研究,在与柳存仁教授就相关文献真伪问题对话之时,就思考为什么一个与西方“圣徒传”一样的传记竟演变成了喜剧化的神魔故事。在他看来,在《西游记》中,玉皇大帝是制度权威的象征,而观音是一种信仰符号,但也不断带上“送子”之类世俗功能,何者为大?缘于这个思考,他专门研究了观音形像的演变过程,并形成了《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The Legend of Miao-shan)为掌握唐人叙事方式,又研究唐人小说的代表作《李娃传》,分析唐代叙事文本形成方式的问题,完成专著《一部中国九世纪传奇的研究与版本评述》(The Tale of Li Wa: 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他在搜辑早期观音传说文献时,发现十世纪中叶流行少女信徒故事与观音形像的世俗化相关,溯其源,以《广异记》中王法智等故事为多,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广异记》研究。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他虽借用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多关注文学问题,关注这种世俗化的宗教体验对于小说结构衍变的作用,这一点在对《李娃传》研究中表现得更明显。其跨学科思维,兼具新旧汉学双重特色。一方面,他有新汉学家学术思维与学科意识,如上述所论,多宏深之论与精邃之思。又一方面,又多有早年汉学家以语言学与文献学为基础的博广之趣,而且,他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这类专著,如《三国典略辑校》(A Reconstruction of Qiu Yue, Summary Documents of Three Kingdoms. Edited jointly with Zhao Chao. Taibei: Dongda, 1998.)《中国中世佚书》(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 The Panizzi Lectures 1999,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0.)无论选题,还是表述方式都是非常本色化的,以积累之功展示了传统汉学的知识魅力,对于中国同行来说,这一特色让人尤有亲近感。杜德桥这一学术风格与学术格局,与他特殊的学缘有关,本科期间他师从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先生,蒲立本就是语言学与史学兼擅的大家,在唐史方面《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语言学上,《晚期中古汉语和和阗语语音的比较》、《古汉语语法纲要》都是国际汉文经典,在蒲立本门下,他掌握了词汇训诂与文史考证的路数,读研究生期间,杜德桥随张沧江先生做论文[5],张氏就是中国古典小说专家,曾翻译《聊斋志异》,这一学术旨趣对杜氏颇有影响。他在读书期间,也多受教于老一辈汉学家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1925-2006),对欧洲汉学传统多有继承,注重解读文本的功底,强调对文献的出处来历的辨识能力。这一学缘使其著作既有传统东方学渊博的魅力,又有新汉学思理逻辑的启发力。 杜德桥《神秘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杨为刚、查屏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1991年,笔者首次接触到杜德桥论文,对其睿智的识见与扎实的功力印象甚深,就追踪他的研究。2001年赴韩任教,试译了他的一篇论文(即本书的第一章),开始与他电邮联系。约在2003年,他委托周发祥先生转达对译稿的肯定并希望完整译介全书。我约在2004年年底完成翻译初稿,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与他讨论了几次,主要是关于书名的翻译。(其时对其全书的主旨尚未把握,对“世俗化”的理念也不清晰,几经商议才译成《宗教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现在觉得译成《唐人世俗化的宗教体验》,可能切合原意。然而,考虑到此题是与他商定而成的,就仍保留下来了。)周发祥先生原拟编纂一套海外汉学丛书,本书列入其中。然而,丛书尚在筹备中,杜德桥与我遽然失联(后知杜德桥先生突患帕金氏综合症),不久,周发祥先生也撤手归山,此事就搁置一下了。在这期间,我用译稿作为备课材料,发给相关同学阅读。印象中,有三位本科生,二位硕士,二位博士已将之作为论文的参考书。杨为刚博士2002年考入复旦攻硕、博学位,阅读本译稿甚有心得,发表了一篇书评,还对译稿作了修正与整理,并借鉴其中空间理念与民俗学研究方法完成了硕、博的选题与论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颇得博士导师陈尚君教授及相关学者的好评,在我看来,这是本书在中国学界引起的最大的反响,他可能也是本书最认真的读者了。这次出版前又请了吴晨博士对译稿作了全面的校改。吴晨博士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师从倪豪士教授,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有了她的修订,我们心安许多,衷心感谢她的热心相助。还要感谢的人有:陈引驰教授,2001年时他在哈佛大学访学,为我复印并邮寄了本书,让我较早读到全书并顺利开展译事;陈尚君教授,在初译之时,他将方诗铭点校本《广异记》借我长期使用,并提供了相关佚文线索,使得翻译工作方便了许多;姚大力教授,在事过二十年,几乎要放弃的情景下,蒙姚教授向“海外汉学译丛”力荐,方得解决版权事宜,重续出版之事;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与英国学术院出版部助理Portia Taylor女士,他们同意授权翻译伊教授所作“杜德桥教授评传”,使得本书可向中国学界完整介绍杜德桥教授的学术成果。当然,也觉得有些遗憾,提议译书者周发祥先生已于四年前去世,不能看到本书出版了;本书作者杜德桥先生也于三年前辞世,笔者在翻译中,解决了书中二处失考之事,一直想找机会与他当面交流,分享这种发现之乐。可惜的是杜德桥教授来上海参会时,我在日本任教。音讯相通,却无缘得见,只能留下永远的遗憾了。当初译书时,骑车到东外滩闲逛,经过社区图书馆以及不远处的上海理工大学,一色的红砖楼,留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时时会想到天下学缘真奇妙,眼前这些楼会与我译的这书也有关系。这些楼一是聂公馆,曾国藩女婿上海道台聂缉椝之宅,一是当年的沪江大学(现上海理工大学)。张心沧是聂家外孙,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与美国知名汉学家夏志清是同学,后来留学英国并任剑桥大学讲师,成为杜德桥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张沧江在沪江大学读书时,就是曾听过一传教士教授讲过《广异记》,到了英伦,张氏又将之反哺给了杜氏。由此事看,本书对于了解现代东西学术交流对话也是很有意义的。 沪江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还需说明一下,事过二十年,笔者对译稿已不甚了了,这次整理多蒙杨为刚、吴晨博士鼎力相助,解决不少疑难之事,但由于初稿多瑕,失误之处在所难免,其主要责任应由本人承担,欢迎读者多作批评指正。 【本文节编稿刊登于《读书》2022年第9期,作者查屏球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感谢查屏球老师授权发布 。】 编辑:吴心怡 注释 上下滑动浏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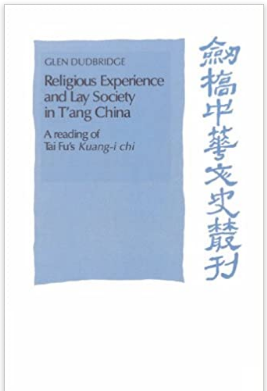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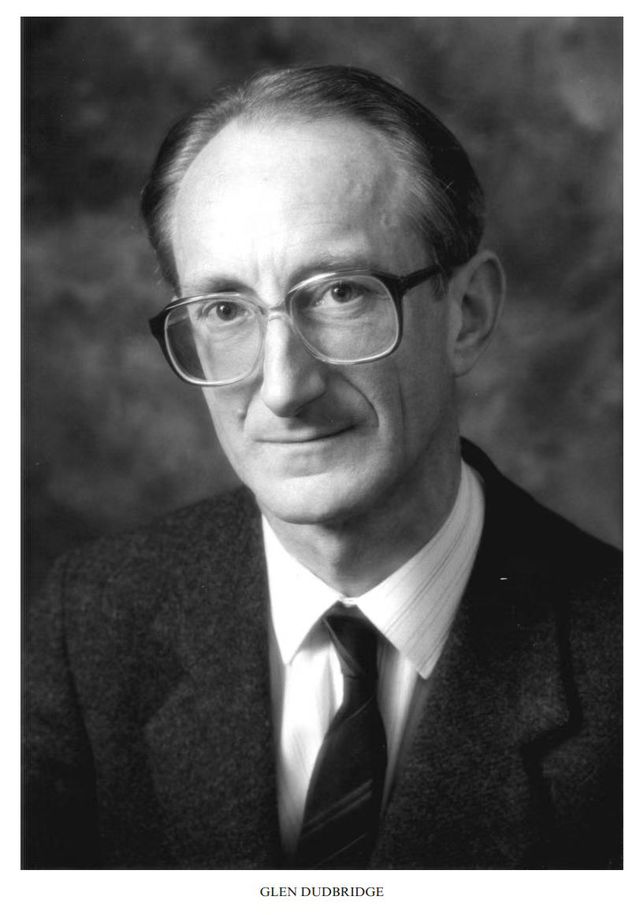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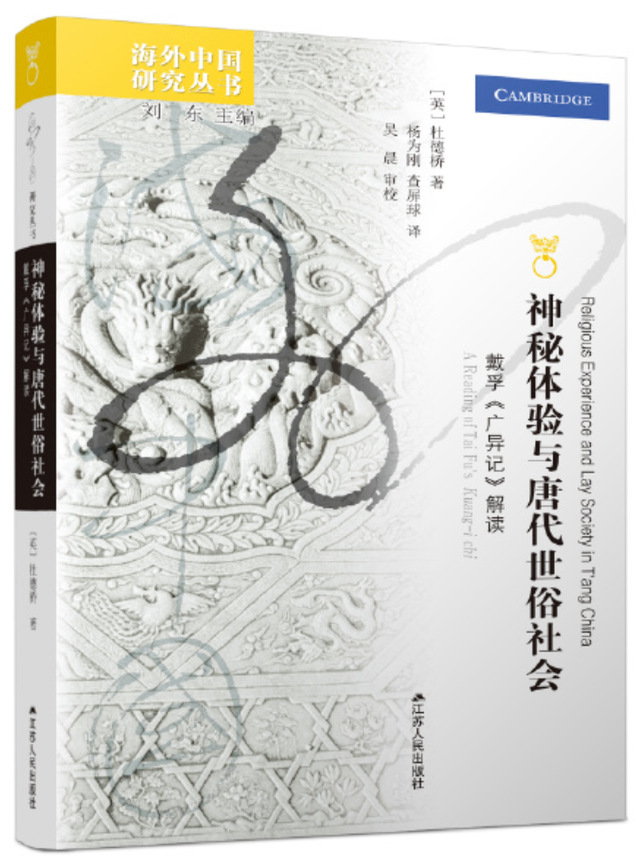


查屏球‖来去自由神俗通
发布时间:
2023-02-22
|
|
|
|
|
|
|
|
|
|
Copyright © 2013 |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电话:021-65643670 邮编:200433
| 历史访客: |
|